生活于方寸之地,也可以海阔天空吗?坐轮椅的才女诗盈正在如此经历。她命定的苦和命定的福是什么?至高的那一位又给了她怎样宝贵的人生礼物?

“远方,一直召唤着我,且有着明显的特质:空旷,辽阔,寂静,人烟稀少。一望无际。这是我童年记忆里全部的风景。”
诗盈出生在新疆马兰基地的部队大院,空旷辽远的戈壁滩是她的儿童乐园。安静自由的空气宛如生命的风,不停地形塑她的生命特质,形成坚韧开阔的生命底色。
因父亲转业,他们一家回到四川老家。那年她十岁,祖籍似乎已成异乡。她听不懂四川话,不适应家乡的生活。两年后,她好不容易融入家乡,一场横祸凭空而来。

一个人和一家人
诗盈患病毒感冒,却被医生误诊,导致脊髓损伤,下身瘫痪。突如其来的残疾,对十二岁的她来讲,是一场生命的灾难。她被学校拒收,出门遭嘲笑,小诗盈感觉被世界遗弃,变得十分绝望。
幼小的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多次想要自弃,可父母想尽办法救治她。当时她并不理解,曾当面质问父亲:“你为什么要救我,不让我死掉?”
父亲很伤心,对她说:“你这个傻女儿,拿刀捅爸爸的心。你知道你活着对爸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希望和开心。”那一刻诗盈明白,为了爸妈,她要活下去。
伴随着诗盈的绝望,母亲也处于极深的黑暗中。病急乱投医,母亲竟然请道士来家里赶鬼,诗盈喝了道士开的符水后,导致更严重的瘫痪,右手也无法动弹。
那段时间,诗盈不想见妈妈。爸爸只好请了一个月的假照顾她。母亲特别自责,觉得女儿的病都是自己害的,想要自杀,被大女儿救下来。
后来诗盈的身体渐渐恢复知觉,可以重新站起来,妈妈才恢复一点信心。她对小女儿讲:“妈妈一定要让你站起来,让你学习走路。为了你,我要好好活下去。”

妈妈带她四处访医治病,身体变得很差,体重只有70多斤(编注:市斤,1市斤=0.5千克)。诗盈那时有80多斤,妈妈翻不动她的身体,就像疯了一样,每隔十分钟就给她按摩脚。在陪伴诗盈的20多年间,为诗盈按摩,妈妈从来没停止过。日复一日,她习惯性地成为女儿的康复师。
妈妈30多岁时,头发全白了,经常染发。有次诗盈陪妈妈去染发,妈妈坐在凳子上睡着了。理发师说:“你妈妈看起来好累!”诗盈知道,妈妈是在用自己的命来爱她。
晚上睡觉,诗盈的脚没有温度,妈妈会搂着女儿的脚睡,要把自己的温度传递给女儿。母亲的爱支撑着诗盈,诗盈的生命支持着母亲,母女二人互相支撑着活下去。
有次妈妈被误诊鼻咽癌,全家人都很紧张。妈妈最不放心的就是诗盈。她让另外三个孩子跪下来,当着诗盈的面,要他们保证,当妈妈不在的时候,三个人要照顾她一辈子,要对她好。那个场面让诗盈刻骨铭心。
哥哥姐姐目睹诗盈如何瘫痪,目睹父母和妹妹的崩溃,看到父母如何疼爱妹妹,他们也学习着爱护妹妹。
一个人的病,牵动一家人的心,凝聚着一家人的爱。

生命的来处与去处
诗盈是医院的常客,常常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因而死亡和尖锐的痛苦成为她生活中的常客。
隔壁病床的患者正吃着雪糕,手一垂就死了;一个全身烧伤的小孩子,持续一夜的惨叫,让她终生难忘。
这些画面和声音刺激着她的神经,她开始思考人最终会去向哪里。她希望有一个天堂,那里不再有痛苦。
诗盈涉猎过佛教方面的书,想借此缓解精神的痛苦。可是看到那些雕像,她觉得凶神恶煞,有些可怕;她也不喜欢寺庙里香烟缭绕的氛围。最让她不能理解的是,佛教认为,生老病死大都由欲望而来,鼓励信徒灭欲。可她觉得,人活着不可能没有欲望。这无法解决的困惑,让她无法接受佛教。
同时她读到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描写基督徒的葬礼是唱诗为死者送行。那种美好的场面很吸引她——不需要磕头跪拜,哭丧摆宴。那些文字是对她探索永恒归宿意识的启蒙。
可诗盈有一种质疑精神,使她不能随便接受信仰。与上帝相遇的路,她一走就是十年。
起初,她无法接受传福音的方式。有次,妈妈陪她在桥上训练走路,一位大叔一路跟着她,大声说:“小姑娘,你赶紧认罪吧,认罪你的病就全好了。”那些行人就都看着诗盈,这让她很气愤。
还有一次,正值下雨天,她摔了一跤,裤子上全是泥巴。妈妈的同事看见后,却不停地讲“感谢主!感谢主!”,她完全不能理解。回到家就对妈妈讲,以后再也不要让这同事上门。
对幼小的她来说,没有弄清楚“上帝为什么要把我变成残疾人”这个问题,她就没有办法信主。那些简单直接的传福音方式,更让她对信仰抵触很深。

妈妈的同事一直没有放弃,她用各种方式向诗盈传递好消息。她知道诗盈反对她到家里,就把一张光盘放在一位老姐妹的杂货摊那里,杂货摊就在诗盈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让老姐妹把光盘转交给诗盈。
诗盈拿走之后很长时间根本没看。直到妈妈的同事再次询问,她才想起来,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趁睡午觉的时间播放。可播放的过程中,她还是睡着了。
醒来时,恰好听到一句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1)
那句话触动她的心,她缺的正是这种内在的支撑力。于是她从头听起。
那是一个见证集,讲这句话的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当时他正在读博士。完整听完一遍,诗盈发现,他所谈的信仰恰是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刻,她没有质疑。
亲情会给她情感上的支撑,但不能带她进入永恒之门。她需要一个永恒不变的力。那一刻,她找到了。
“生命有来处,自然有去处。死亡不过是中转站。”这是诗盈多年后的文字,她对死亡与苦难已经有了深刻清醒的认识。

人生最棒的礼物
2003年11月,诗盈和妈妈一起走进教会。三个月后,她的灵魂伴侣从“天”而降。和李虹相识,是诗盈生命中的一个奇迹。
有天晚上,她对上帝低语:“如果你存在,我就把心里话告诉祢……我希望祢能把我带到一个不冷的地方,在那里我能遇到终身伴侣。他最好有文化,性格也好。”这是一封遥寄苍穹的书信。
三个月后,她收到一封邮件,寄信人是李虹。信中说,他用一晚上的时间把她在论坛上的所有文章读完。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感觉冥冥之中,你就是能够和我一辈子走下去的那个人。”
诗盈读过李虹的文章,知道他是北大物理系毕业,个性独特,相当有才华。可当时仍然很吃惊:这个人好奇怪,第一封信就表白,她可能是能够和他携手走一生的人!不过,她没有拒绝邮件往来,愿意更深了解彼此。
诗盈说:“我不相信网恋。”李虹很爽快地回应:“那你五一过来见见我,以及我工作的地方——深圳。”
那是诗盈的第一次远飞。她心里忐忑不安,包里放着圣经。她对上帝说:“这一路就靠祢了,我要找的是同路人,请祢一路带领。”

飞机晚点七八个小时,他们终于见面。一位义工推着李虹,在机场迎接她。诗盈和李虹平时面对异性都比较紧张,但他们初次相见却像老朋友,似曾相识。
他们都是后天残疾,都有被世界遗弃的痛苦,情感上很有共鸣。更奇妙的是,他们的个性也很相似:很简单,有闯劲,不太认命,有一股傻气,不太把物质生活当回事。
深夜的一次低声倾诉,上帝却很慎重地放在心上,这么快就给了印证。这让诗盈对神的认识又加深一层。
很快李虹去慕道班并受洗。他们举办婚礼,在众人的祝福声中,进入婚姻生活。

方寸之地的海阔天空
他们共同生活的18年间,李虹每年都会被送去急诊。
一次清早,他突然发生状况,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诗盈当时已经坐轮椅,无法送他去医院。她想起教会一位姐妹在附近上班,赶紧给她打电话,姐妹请假到她家。又打电话给社区,社区派两位社工,并联系医院,物业人员也快速赶来。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李虹被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救治。
诗盈很怕遇到这种情况,可真正遇到之后,她发现:神都有预备,只是她必须踏出第一步。
同类情况他们又遇到过很多次,常常是到医院没有床位,医生看到他们不容易,会找其他医生,设法在另外科室帮助他们安排床位。他们一次次经历神“早有预备”的祝福。
长期疾病给他们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李虹一个月的心衰药物需要一千多元钱,为给丈夫治病,诗盈一直很节俭。她甚至想过要搬出电梯公寓,去找一个小的房子。
当她说起自己的想法时,李虹却说:“不用搬,上帝会预备。”诗盈觉得丈夫不接地气,不考虑现实问题。
奇妙的是,就在第二天,李虹的两个高中同学一起来看望他,带来了一箱中药和六万块钱。她觉得很不可思议,如果说是巧合,在神里,巧合好像太多了吧!
当叙述这些事情时,诗盈感慨地说:“上帝借着不同的手,差派不同的人来帮助我们。这种恩典真是太多了,数也数不尽。”
身体和现实看起来只是方寸之地,供应和盼望却又海阔天空。这可能正是他们生活中命定的苦和命定的福。

这,一滴水的声音
诗盈被劝休学后,一直在家自学自考,完成大学学业。
18岁,她和爸爸一起到单位上班,老板很歧视残疾人。她工作很努力,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当她去领年终奖,老板把她推到经理处。找到经理,经理却说:“你工作干得很好,可惜你是残疾人。”残疾,成为同工不同酬的理由。这让她倍感受伤。后来她辞职,自设书屋卖书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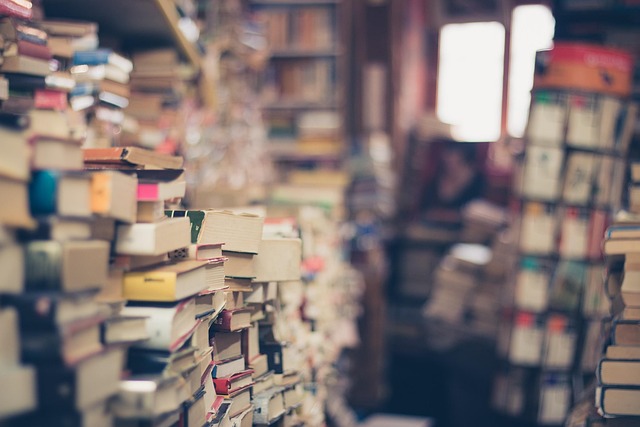
再后来她做会计,上班需要坐公交,那又是一次次的挑战。她行动比较慢,经常在站台等半个多小时都上不了一辆车。车不会正好停在面前,她需要慢慢走过去,有时还没走到,司机就不耐烦地开走了。有次爸爸陪她一起出行,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大骂。诗盈劝爸爸不要发火,因为这就是她的生活常态,也是中国残障群体的生活常态。
亲身经历诸种事件后,诗盈开始关注社会的基建设施以及残障群体的生活权益,有意识地在推进残疾人无障碍出行方面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她会给相关部门提意见,或者就某些不公的事件投诉。她说:“作为残障群体的一员,我不投诉很少有人知道这些。”
诗盈的声音可能微小,但总算有人出来为这个群体发声。即使只是一滴水的声音,也可能给沉默已久的深井,带来一次小小的震荡。

我将要前往的远方
婚前,诗盈独自记录自己的生活;婚后,夫妻二人彼此陪伴着书写。
李虹是理工男,想在文学上有所突破,诗盈鼓励他写博客文章;看到他想象力丰富,且童心未泯,诗盈又鼓励他写小说。恰逢香港举办一个儿童圣书故事大赛,他投一篇文章参加比赛。
当时李虹对自己能否文字侍奉很不确定,他想向神要一个印证:“如果我能做文字侍奉的话,就让这次参赛(的作品)能够入选。”结果好几个月没有动静,就在李虹认为已经没希望时,通知来到:他中了儿童故事首奖。
初试啼声,就中头奖。两人都认为这是神给的一个印证。从此,李虹开始微信公众号(“罕声”)的写作生涯。他自称是“特种兵”和“潜伏的侦察兵”,以文字为探照灯,为许多同处困境的人照亮前方的路。
诗盈的写作则有些不同。之前她就经营公众号,并在线上工作,做新媒体编辑。有段时间她眼睛受不了,让李虹帮助处理图片。当他学会后,开始做公众号,她却进入写作低谷期,厌倦了写作。直到她参加创世纪文字培训书苑的回忆书写课程,这种状态才得以改变。
诗盈有病时,弟弟还不足十岁。父母全身心投在她身上,忽略了弟弟,他的性格因此有些孤僻。所以,长期以来,诗盈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不停地指责她:“都是你的错。一家人因为你命运被改变,家里经济困难,都是因为你。是你害了弟弟!”那是她长期背负的灵魂之重。
课堂上,进行内省书写时,对家庭和弟弟的罪疚感再次涌进来。她无法书写,不停地流泪。莫非老师了解情况后,对她说:“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问题。”这句话治愈了她。那次文字营中,她领受写作的呼召,重新开始公众号(“诗盈的一亩田”)写作。

这条路并不好走,当时的信仰写作通常比较高调,而她常常是趴在地上写。
她想要记录自己的生活,为残障群体发声。所写大都是日常生活故事,这是很多患者亲身承受却无法写出来的生命经历。很多人在后台留言,说被她的文字理解并鼓励到。
诗盈说:“我的文字不是大调的,而是小调的。有人坐着写,有人站着写,我是趴在地板上写。”写作的姿态不同,看到的人性与世界也不同。
诗盈夫妇变一行行文字为人性的触角,伸向世界与人心更深的地方。他们的笔始终指向灵魂自由的方向。

爱,远远大于爱情
李虹的母亲很辛苦,先是照顾李虹奶奶到93岁,接着又照顾儿子。诗盈夫妇商量,到父母70岁的时候,要找一个看护,卸下他们的重负。可是在老人满70岁的时候,李虹却被神接走。
李虹是最佳病人。他从来不对父母发火,一直都是笑嘻嘻的。他的乐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他对神从来没有质疑,常常对妻子说:”你不要问为什么!神给我们的命运,我们去承受就好。”
诗盈认为,丈夫对残疾的理解很独特,甚至是颠覆性的。
他说:“很多人觉得残疾是不幸,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世界上只要有健全人,一定会有残疾人?神拣选我们做残疾人,让其他人没有残疾,健全人应该感到幸运。”李虹的观念,让诗盈很震惊。
李虹离世四天前,还在更新公众号,写最后一篇见证。身体受限,生命无限,短短一生,他活成见证祂的亮光。
采访中,诗盈说:“李虹走后,我感觉到,我现在好像变得越来越像他了。”
她以前比较多愁善感,现在看开很多;以前对自己有很多批评,现在比较能够放过自己。这是爱人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对上帝的信靠,已经内化在她心里。
在诗盈眼中,李虹以上帝的精兵来要求自己。他离世前的那段时间,好像在打一场艰难的仗,有一种战死沙场的士气。
保罗曾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后4:7)
诗盈认为,爱人做到了。采访中,诗盈对记者说:“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当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也能说这样的话——对神说,对人说。”
“相守十八年,一路上有你。你已去,祂还在。”路跑尽,道守住,这是相爱之人的彼此期许,也是对更高之爱的共同奔赴。
“路跑尽,道守住,一路上有祢”,这大概是每个神儿女的心声。宛如一滴水经过九曲回肠,最终注入大湖,是每滴水的心愿。
注:本文题目和小标题全部来自微信公众号“诗盈的一亩田”的文章题目。
作者简介
创文公关同工,前新闻主播/记者。目前为《真爱家庭》杂志、《神国》杂志采访及撰写文章。
两个孩子的妈妈,中学老师。热爱读书与骑行:穿梭于文字与街巷,总能发现深藏于生命与世界的热情与美好。曾因他人的文字而热爱生活,也愿自己的笔能给他人带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