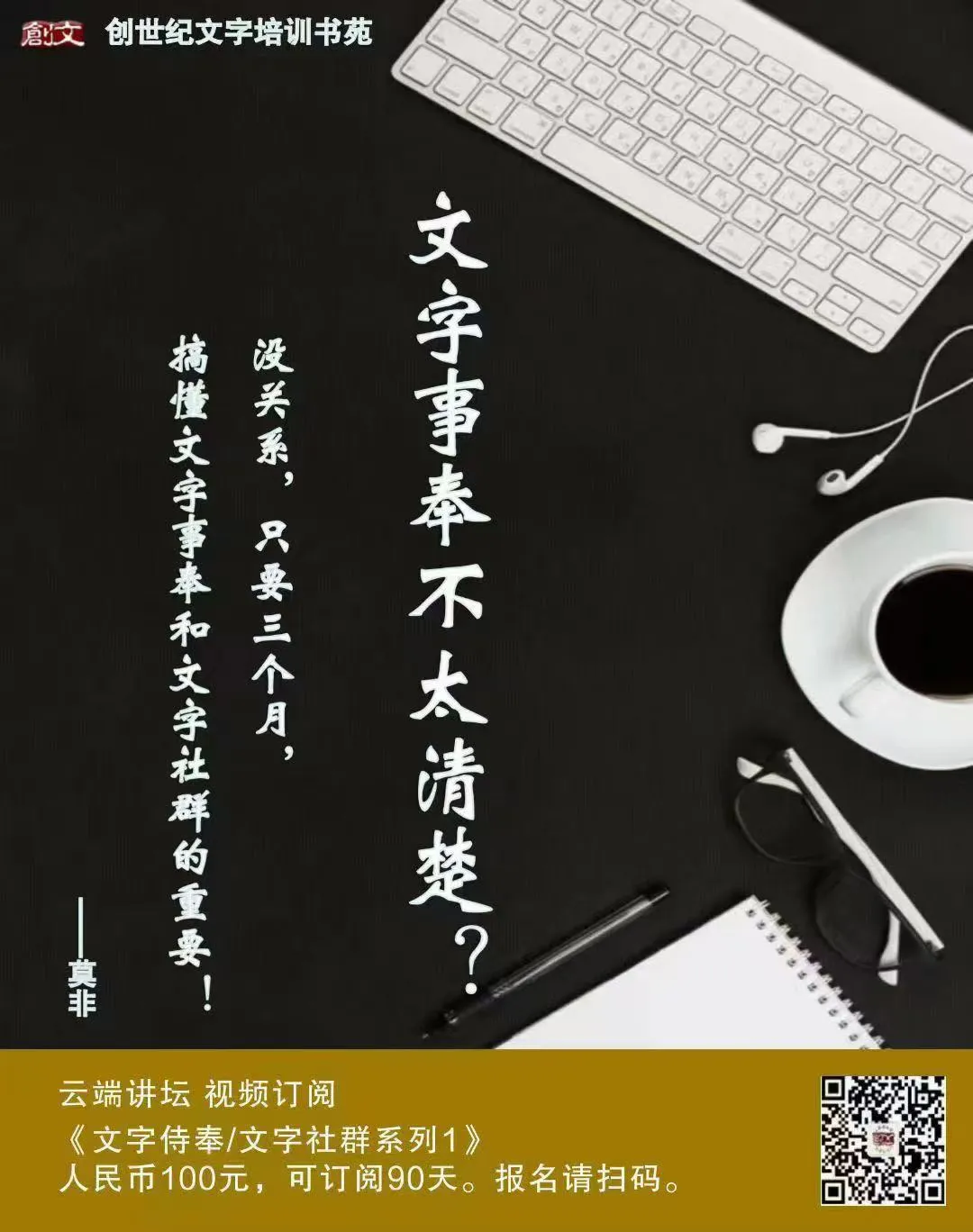服事中用得上语言的地方有很多,但如何才能使用恩典的语言,传递祂的心意?在我们的口袋中,恩典的余粮有哪些?
文字事奉不太清楚?三个月搞懂文字事奉和文字社群的重要。欢迎查看文末海报,了解云端讲坛《文字事奉/文字社群系列》课程。


每次站讲台都会自问,我传讲的“道”是让会众感觉神国更大,还是更小?体会到的信仰是更鲜活,还是更僵死?神的话语更触手可及,还是更遥远抽离?
上台前一遍遍走稿的时候,也会想,坐在下面的会友是从什么样的生活中走来听道?外表穿得光鲜亮丽,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否乌烟瘴气?家中是否弥漫硝烟?心中是否有重担或焦虑?而我带给他们的,是法利赛人的枷锁?还是主耶稣轻省的轭呢?
这些问题会让我每次准备讲道时,选择的主题和经文都必须能先挑战自我,并且点燃自己的灵魂,才感觉稍可传递给人一点温热。也深知自己的斤两多少,不求自己的语言可以点燃,但求可以稍稍温暖或点亮他们的灵魂。
但是恩典的语言,除了讲台上的教导或讲台下的辅导,应该还有许多机会可以不着痕迹地传送吧?平常的文字社交互动,或面对面的聚会接触,是否从灵魂的口袋中都可随时随地掏出呢?重要的是我灵魂的口袋中,是否储存了足够分量的恩典祝福?
即使讲员或做教导的人自己,都会怕听到信仰中的陈腔滥调,也都渴望接触信仰中的清泉甘露。然而我们自己开口,是否让人有如吸到一口山中空气,瞬间感觉到整个人被更新呢?这又需要多少的祷告和更新而变化的心意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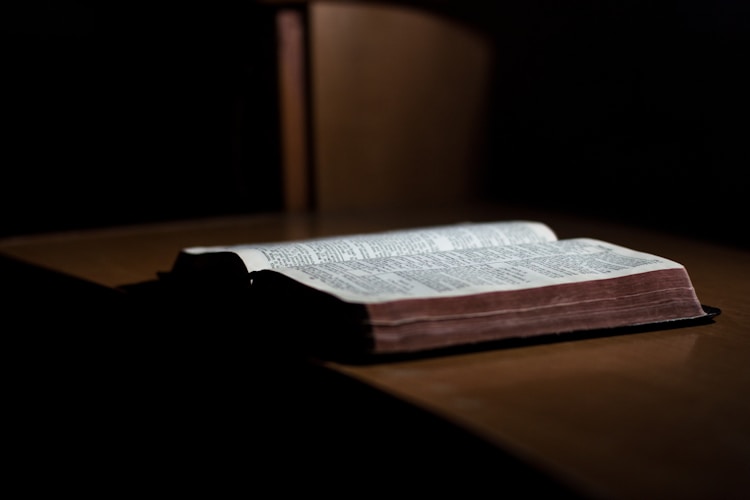
我曾说过,文字事奉最大的挑战,是不把信仰写得过浅,而是写得深。
何为过浅?就是随意套用属灵八股或者术语,没有经过个人的生命诠释或生活应用,就硬塞入对方的脑中。不幸地,这些常沦为无意义的口号。更不幸地,是对人的苦难处境不但没有安慰,反而成为定罪。
但何又为把信仰写得深呢?就是自己曾在生活中不断地操练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中领受属灵的洞察和智慧。然后,勉力而为地用各种创意方式,呈现信仰的鲜活和丰富。
这已非修辞或文学技巧可以帮忙了,而是从我们生活的底蕴中提炼,并有圣灵的启示和洞察,盼能把人的苦痛呈递到神的面前求告;也能把神的心意再一次“翻译”,传送到人的心中,就如大卫的诗篇。
然而在恩典的口袋中,我们是否常会觉得“囊中羞涩”,掏不出来呢?
恩典的存粮是否囊中羞涩?
服事中用得上语言的地方其实很多,这是为何我常会说:提升语言智力,就是提升服事的影响力。从异象分享、属灵教导、人事协调到个人关怀,哪一项不需要语言呢?
然而我们中大部分人走上服事,都是出于负担,不是出于恩赐。我们的负担常常大过我们的恩赐。在语言方面我们也会像摩西,说出:“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出4:10)
更何况人生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名言:“生命中,总是会有连舒伯特都无言以对的时候。”
是的,人生有太多时刻,会让天天和语言打交道的我们也感觉无语。这已非简单地“做文章”了。写文章是按照自己对普遍人性的了解单方面诠释表述,但是,安慰一个独特的灵魂,需要针对这个人的特定处境来传递神的爱,以及带给对方些许亮光。
如果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未有存粮,就很难拿得出什么来喂养他人。这个存粮包括我们自己对神的亲身经历和解读。在我们心中,神是慈爱的神,还是审判的神?对苦难,相信这个神会出手解救,还是沉默地允许发生?这个灾难频发的世界,到底是谁在掌权?这发生的打击,是因为神的管教、处罚,还是人的罪?

存粮,也包括我们对自己生命中的失去,是怎样回应?我们曾经对神质疑或者愤怒吗?我们曾经拒绝他人的关心和慰问吗?我们的伤痛中,是否夹杂自怜、自责或者绝望的感受?我们自己被哀伤淹没时,是否会伸手求救?我们自己是否曾从“失去”中成长?是否可以跨越苦难中常问的“为何发生”(Why),而踩进苦难后的“如何自处?”(How)
存粮,更包括我们对死亡是否恐惧。我们是视死亡为破坏、分离我们的残忍敌人,还是一道必经的关口?还是,死亡是一通往更充实、更荣耀的凯旋之路?对死后身体的去处,对如何面对生离死别,以及对天堂的认识和想法,我们曾经思考过吗?
张文亮的妻子屈贝琴临终时,在最后气息中曾留言:“你要赞美。”何其让人向往!好似死亡乃是一路赞美神的途径。事实上,许多宣教士也是在赞美中被主接走,我们对这样的结局向往吗?
恩典的存粮,是靠平时的积累。积累愈多,可以拿出的选择也愈多。我们是一个平时常往自己灵魂口袋存恩典的人吗?
作者介绍

课程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