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天主教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新片《伊尼舍林的女妖》承袭他一惯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一段友谊断裂的故事。片中主角提出的:什么是友善?什么能永垂不朽?值得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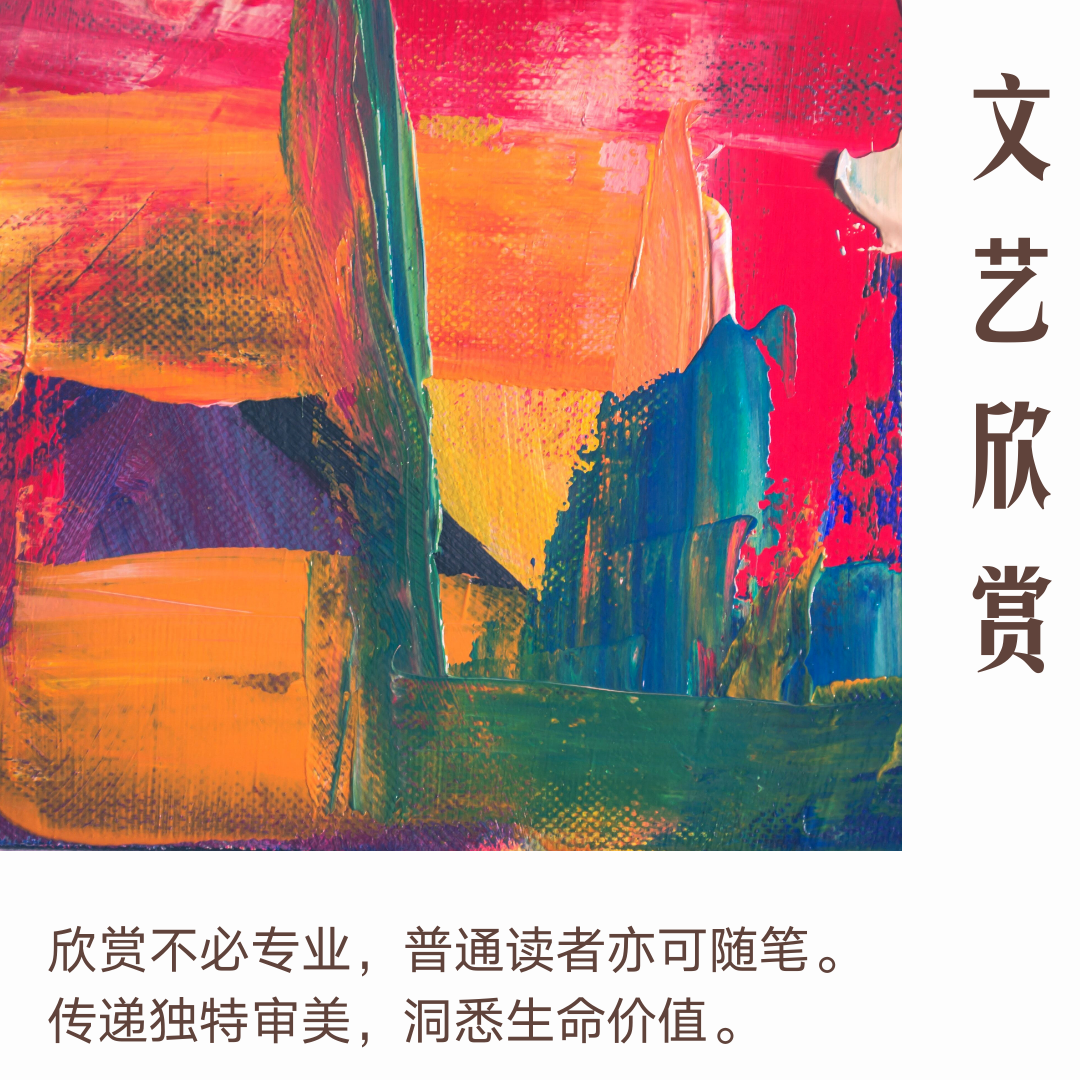
这是一个位于爱尔兰海岸外的神秘岛屿——有大海、悬崖、薄雾、日出和日落,仿佛伊甸园,一个未受破坏的天堂。岛上有一所教堂、一个酒馆、一间邮局,岛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然而,就像第一个伊甸园,以及此后的每一个伊甸园一样,它不会持久。由于第一次的血腥和残暴,人类罪恶和苦难的古老故事在这一切美丽之中展开。
爱尔兰天主教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新片《伊尼舍林的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承袭他一惯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1923年在一个名为伊尼舍林的岛屿上,一段友谊断裂导致精神世界崩塌的故事。在时空背景与爱尔兰内战遥相对照下,麦克唐纳试图从两位老友关系的决裂开始,描述岛民的精神状态。影片探讨生存焦虑、疏离、孤独与生存的意义。
电影情节再简单不过,单纯知足的年轻小伙子派瑞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性格单纯开放,热爱他照顾的牛、小马和名为珍妮的驴。年长的音乐家康姆是一名热爱创作、一心投入音乐与艺术的人,家里有留声机,随时都播放着古典音乐。派瑞与康姆原来是一对挚友,20年来每天下午两点钟准时在镇上酒馆喝酒、吸烟、聊天。

突然有一天,康姆单方面宣布绝交,理由是他不愿再浪费时间听派瑞无聊的言谈,希望把余生用来创作音乐,留下有意义的精神遗产。这个消息对派瑞如同晴天霹雳,他从受伤、无助到愤怒,三番两次试图挽回两人友情,却始终无效。这些激化康姆升级采取暴力行动,甚至扬言要砍断自己的手指,以表明分手的决心。
“好像没什么人在拍悲伤的电影了。”导演麦克唐纳在一次受访时这样说。在战火轰隆的大环境下,他以深沉的悲伤为底色,烘托出这个挚友分手,笑中带泪的黑色喜剧。
岛上唯一看透真相的似乎是派瑞的姊姊希布,她也是村子里唯一一位长年阅读的知识分子。当她得知康姆宣布与弟弟断交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都太无聊了!”她厌倦镇上的琐碎、八卦与日常生活。后来由于弟弟与康姆的战争,她被逼到极限,决定离开牢笼般的岛屿,前往另外一个战火隆隆的大陆。
希布的离去等于对派瑞的第二次重创,正如杂货店老板娘的警告:“如果你离开,你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失去挚友和姊姊之后,派瑞的生命崩塌如同被钉十字架,唯一的安慰是对动物的爱。后来,他心爱的珍妮无意中被康姆杀死,成为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古至今,人类腐败、自私、残忍的罪性不变。
康姆对派瑞的自私与残忍(包括决绝地宣布分手,砍断手指以示决心,间接杀死小驴)导致这位单纯的前挚友从一个外表上看似的好人,变成了狂暴的复仇者。最后他疯狂放火烧掉康姆的房子。影片最后一幕两人站在海滩上,眺望大海对面的大陆,大战似乎正在平息之中,派瑞痛苦地表示,他们之间的小战才刚刚开始。

出生于爱尔兰家庭,在工人阶级、教堂、天主教学校里成长的麦克唐纳,虽然声称不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血液里澎湃的爱尔兰情感与天主教文化标志、符号和语言却都清楚地铭刻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
无人可以免除罪恶。看似天真无辜的派瑞,善良的外衣一旦被揭开,野蛮的罪性明显可见,而复仇的欲望更让他越陷越深。随着电影结束,我们看到无论派瑞或康姆都没有好下场,因为他们早已被困在自己的精神荒岛上。就像但丁的故事一样,这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地狱。麦克唐纳将这种天主教的罪恶观戏剧化,同时也将教会描述成无法帮助人们承担苦难的制度化场所。
影片的第一幕,圣母玛莉亚的雕像俯瞰着在周日进出教会的村民,如同岛屿上其他所有石头一样,没有生命,除了凝视远方之外,毫无用处。在岛上游荡的那个干瘪、头上披着黑巾的麦考密克夫人预言死亡和厄运,她是电影片名女妖的替身。 岛上在周日会分发圣餐的天主教神父,对于处于绝望中的康姆毫无帮助,无法同理他的精神荒凉。在一幕情节中,康姆问神父,拒绝和朋友说话是否是一种罪过,神父回答说:“不,这不是罪,但这不是很好。”
康姆自认为拒绝好友派瑞的友情无疑是某种罪过,就像彼得否认耶稣一样,是对忠诚、仁慈和爱的背叛。主耶稣发出的两条诫命中,第二条是爱人如己,康姆在这点上失败了。这是一座破碎的教堂,不了解自己的神学,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了解自己的故事。唯有神的爱才能将我们从自我与内心深处的阴暗角落里拯救出来。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没有爱,就没有希望,没有生命,没有上帝。
在这个岛上,敲响丧钟的女妖获胜。
有人认为麦克唐纳的电影艺术与美国小说家奥康纳的文学创作风格近乎雷同,两人都擅长用黑色幽默包装暴力、道德与人性的主题。 奥康纳的作品常被描述为“南方哥德式”小说,以怪诞的人物与场景为特色,探讨人性与社会规范的黑暗面。
不约而同地,麦克唐纳的舞台剧和电影也经常出现黑色喜剧场景以及有暴力倾向的角色。除此之外,两位同样出自天主教背景的艺术创作者,作品中都融入天主教与道德的主题。奥康纳笔下的故事常围绕罪恶与救赎的议题,而麦克唐纳的作品则讲述在道德困境与行为后果中挣扎的小人物故事。
影片里,在两位男主角的一段经典对白中,康姆直接挑战“友善” 的观念。他说“友善”不持久,但是音乐、艺术与诗的创作却能永垂不朽。派瑞不服。

康姆:“谁记得17 世纪哪一个人以友善出名?但是大家都记得创作音乐的莫扎特。”
派瑞:“莫扎特是谁与我无干,我们现在讲的是友善。我妈妈、我爸爸、我姊姊,他们都是友善之人,我永远记得。”
康姆:“50 年之后谁记得希布和她的友善?谁记得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但是活在两世纪前某人创作的音乐,大家却记得清清楚楚。”
派瑞后来被姊姊劝诫回家,路上喃喃自语:“我不管什么莫扎特、贝多芬,我是派瑞·苏立汉,我是一个友善之人。”
居住在北美社会,常听人用“nice guy”形容某个好好先生。这个形容词有时候变成了反讽赞美的同义词。影片中,康姆认为派瑞口中的“友善”换句话说就是“庸俗”,他无法继续忍受派瑞的平生无大志与缺乏生命激情。但是在长达20 年的友情里,派瑞始终如一,康姆从未因此拒绝和他在小酒馆聊天啊。他的翻脸无情让两个悲情人物的感情走到尽头,导致一场悲剧的发生。
人际关系学问大。友情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它跨越血缘、地域、国籍、社会地位、学识与家庭背景。两人的生命之流能汇聚一处,有所共鸣,有所交流,本该是件美事。但是人终归是人,我们里面的七情六欲有时受到环境时空的改变,而让人一时冲动做出失去理智的决定,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翻开圣书,我想到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爱人如己”,使徒保罗提醒信徒们“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将信与爱当成生活的底色,方能在社群里活出永生的盼望。
麦克唐纳透过本片直指人类灵魂中的黑暗,是对未来即将到来的黑暗敲响的一记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