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此我说
- 07/22/2025
刘嘉:我们为何这么快遗忘?——从6位实习生溺亡事件说起
作者:刘嘉
屏幕时代,新闻、娱乐、广告一气呵成,正潜移默化地传递一种态度:没有一条人命珍贵到不能被一个轻松段子快速替换。对此,我们可以有怎样建设性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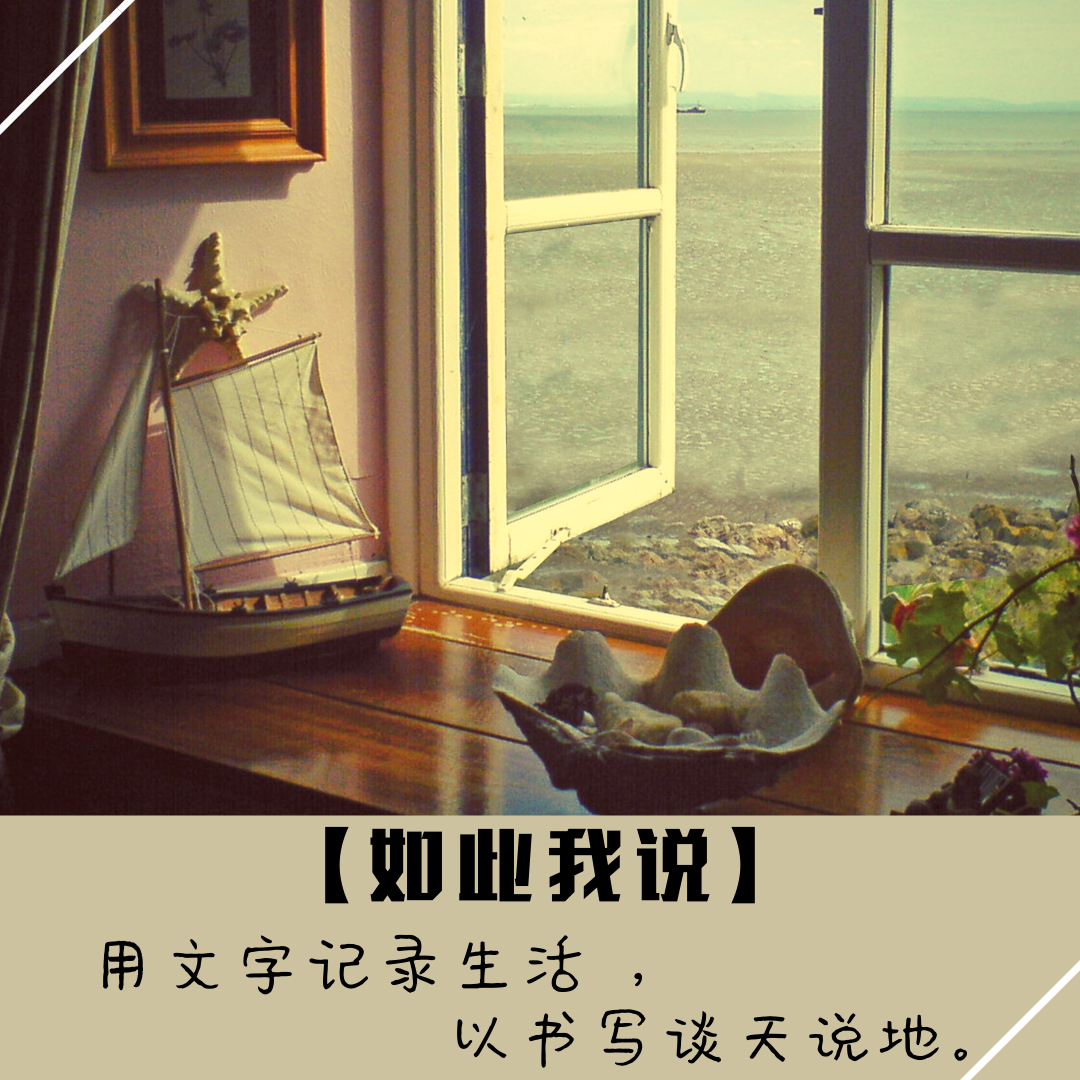

7月23日,东北大学6名大三本科生在参加矿业企业实习途中,不幸坠入选矿厂浮选槽溺亡。他们的生命,就这样在一次实践教学中戛然而止。事件立即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提级成立事故调查组,中国黄金集团及涉事矿业公司停产,自媒体舆论、媒体报道、人心哀痛,迅速形成舆论场。
但让我难以忘怀的,不只是这起事故本身,还有它在我手机屏幕上所处的位置。就在我浏览这起沉痛消息的同时,另一则新闻赫然弹出——“全球每年近1000万人到印度旅游,哪些人更爱去?”标题轻快、配图明艳,与上一则令人心碎的事故形成极端反差。
这不是个例。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类似的情绪“抽离”——刚刚为一个悲剧流泪,下一秒却在笑看网红旅行日志;刚因社会不公愤慨不已,随手一滑,却又被宠物视频逗乐。新闻与新闻之间,没有过渡;感情与情绪之间,来不及发酵。于是,我们遗忘的速度越来越快。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在今天的热搜上也许已经消失,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好像有这么件事吧。”
碎片化世界,让悲剧变得轻浮
媒体有多“任性”,任性到它可以决定我们“看见什么”,因此“在意什么”。当我们坐在电脑前或滑动手机屏幕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整个世界,而是被挑选出来给我们看的世界。而我们心中所谓的“事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些画面拼贴出来的。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那本叫《娱乐至死》的书里有个经典论点。他说,新闻总喜欢用“刚刚……现在……”来过渡,比如:“刚刚报道的是台风灾难,现在我们来看看体育赛事。”这不只是一个无害的转场语言,而是潜移默化地传递出一种态度: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被认真对待太久。没有一场灾难是那么沉重,以至于不能被一个体育赛事视频迅速稀释;没有一条人命是那么珍贵,以至于不可以被一段轻松段子快速替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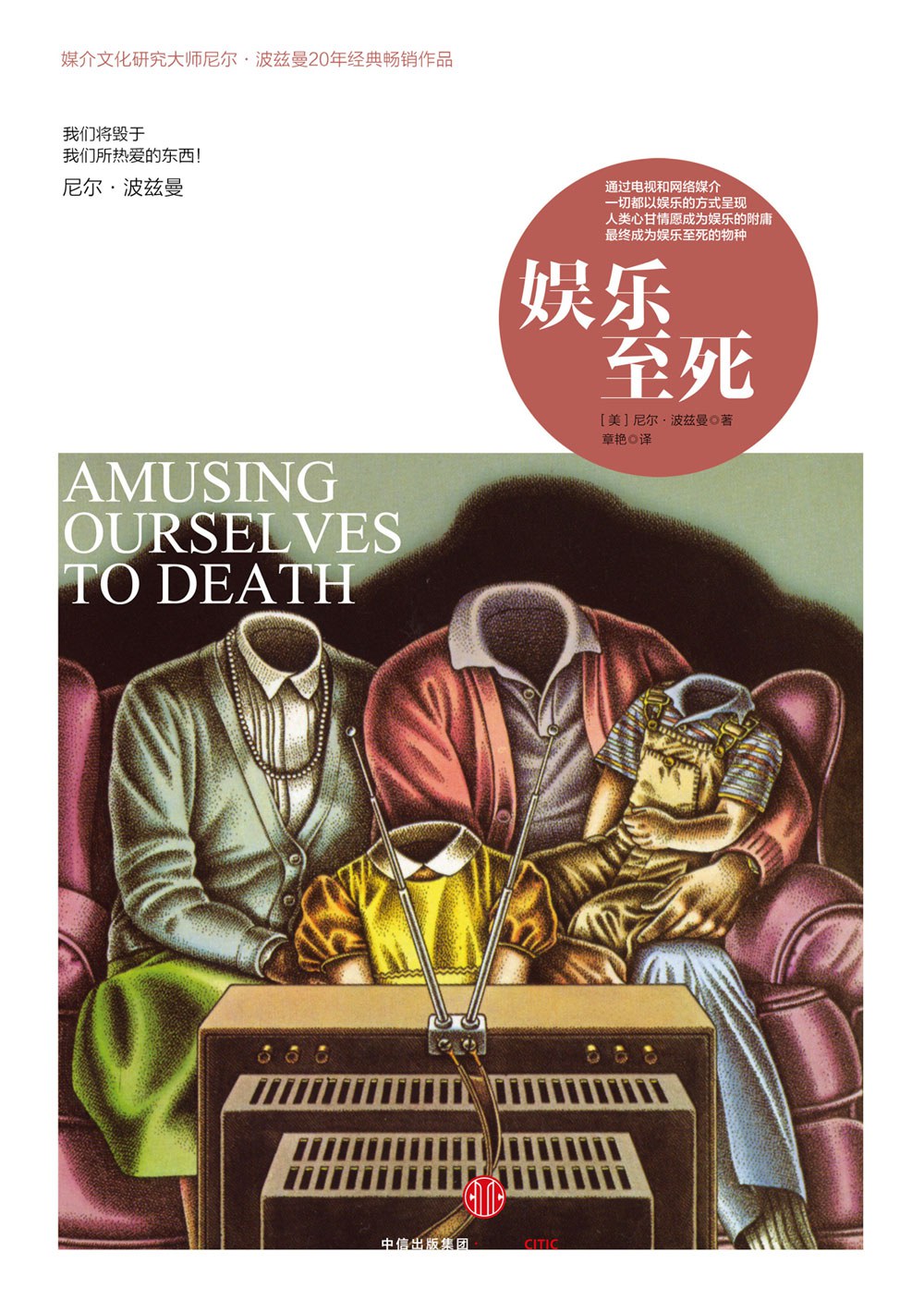
我们逐渐习惯了这样碎片化的节奏。不连贯,不持久,不深入。正如波兹曼所说,这样的媒体结构抗拒深思,它让我们知道得很多,却理解得很少;情绪很激烈,行动却很迟缓。
现代互联网时代,新闻、娱乐、广告一气呵成,逻辑与伦理不再是新闻的核心。数字媒体的本质是流动与切换。你点开一条新闻,看完东北大学的事故报道,再滑一下,就是印度旅游人数的报告;再滑一下,是明星八卦、健身教程、直播带货。你的眼睛还没眨,情绪已经完成了从哀痛到娱乐的三连跳。表面上你参与了公共话题,实际上你只是经历了一次感官刺激。
你记得那6名学生吗?他们的名字是?他们来自哪里?父母是否受到妥善安慰?责任人是否已经查明?安全制度有没有改变?这些问题,在情绪被稀释之后,就很难再激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的思考被浅化为“哇,好惨”或“吼,这个国家真热门”,真正去理解事件原委、追问制度责任、思考生命意义与安全制度建设的可能性往往被压缩甚至完全丢失。这并非仅是风格问题,而是整套信息机制——速度至上、易读至上、反应至上——在主导。思考稀缺,反应成为默认;反馈迅速,却不建立深度理解。
社交媒体,让感动变得廉价
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一书中指出,数字媒介正在重塑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更容易接受图像而不是文字,更偏爱短小而非复杂的信息,更擅长情绪表达而非逻辑推演。于是,新闻也就相应改变了形式:标题党、情绪渲染、剧情化叙事成为主流。你可能会因为一段母亲失声痛哭的视频而落泪,但未必会点击后续调查的长文;你可能为那6名大学生的父母发出一声叹息,但未必会留意这起事故之后的相关改革。

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媒体让所有信息并列出现,没有主次之分。一条新闻说“大学生实习溺亡”,下一条却是“明星在综艺节目中落水大笑”,两者同样大小的字体、同样热烈的评论区,把生命与娱乐并置,把哀痛与搞笑拉平。
这让我们逐渐丧失了一种能力——恰当地感受的能力。我们不再知道,什么该伤心、什么该愤怒、什么该冷静思考。所有情绪都被调成中间值,像是调和漆,哪怕最惨烈的事件,也能被稀释成“哎呀,真遗憾”。
在碎片中寻找有意义的停驻
面对如此环境,我们不是没有选择。我们不能改变整个媒介生态,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待信息的方式。我们可以选择慢下来,选择认真地“看”一条新闻,选择不在悲剧面前轻轻掠过,而是愿意“停驻”,哪怕只是一分钟的默祷、一次深入的阅读、一次良心的不适。
以下是几个具体的操练方式:
限定使用时间:设定每天固定的媒介使用时间,而非全天候滑动。比如早上看一次新闻,有空再做一次反思。
明确使用目的:不是无意识刷屏,而是带着目的浏览,比如“我要了解这起事故的最新进展”“我要找一篇深入报道”。
选择合适载体:重要事件,尽量阅读长文或权威调查报告,而非只看热搜标题和情绪化视频。
建立核查意识:多看几个角度,不轻信网上消息;愿意查证,也愿意花时间理解背景。
恢复“与哀哭的人同哭”的心
我们常以为,转发一条公益新闻、点赞一个正义发声,就是我们对世界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但这只是“最低门槛”的参与,远不足以称为“公义的行动”。
真正的关怀不是点一下屏幕,而是愿意承受那份不舒适。我们要问: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城市、我的群体、我的孩子身上,我愿意做什么?愿意多走几步吗?
真正的参与,是不怕让事件“留下痕迹”在我们心里。比如我们可以关心身边实习的学生:他们知道有哪些安全隐患吗?他们的实习单位合规吗?他们是否具备自我保护意识?
再比如前不久发生在甘肃天水的幼儿园铅中毒事件,当我们看到那些幼儿体检单上惊人的数值时,也许可以问问自己:能否在小组里组织一次祈祷?能否请一位具有公共健康教育背景的弟兄姊妹来分享?能否在朋友聚会中,主动谈谈食品安全这个“冷话题”?

我们不是社会救援队,但我们是有光的群体。在这个习惯于快速遗忘、浅表共情的世界里,我们若能多一分认真,就是抵抗;多一分长久,就是见证。
圣经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世界无法理解的福气。因为在这世界看来,哀恸太不合时宜,太不高效,也太沉重。但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哀恸意味着心灵柔软、眼睛清明。“哀恸”是福,因为它代表我们的良知仍然敏锐,代表我们的心还没有被“刷刷刷”的生活磨钝,代表我们仍愿意站在孩子、弱者、边缘者那一边。
也许,我们无法改变整个社会,但我们可以不让冷漠在我们里面生根。我们可以让天水那群中毒孩子的面孔,变成我们祷告墙上的代祷对象;可以让那句“为了让饭菜看起来更好看一点”,成为我们反思虚荣、拒绝包装主义的提醒。
当我们为那6位大学生哀哭,为他们的父母哀哭,为这个体系中沉默的漏洞哀哭,我们其实正在恢复人的尊严与本相。不是被信息流同化的滑动者,而是一个个真实、敏感、有感受的人。
在信息洪流中保持哀恸,就是信仰的见证。不是逃避世界,而是深入世界;不是沉溺于悲情,而是带着主的怜悯去参与。我们可以在这个容易被带节奏的时代中,选择属灵的节奏。我们不只是共情,也愿意同行;不只是哀恸,也愿意在祂里面活出那温柔与有盼望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