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童书作家凯瑟琳·朗德尔毕业于牛津万灵学院,然而与传统学院派不同,从小在非洲生活的经历,赋予她不同的写作视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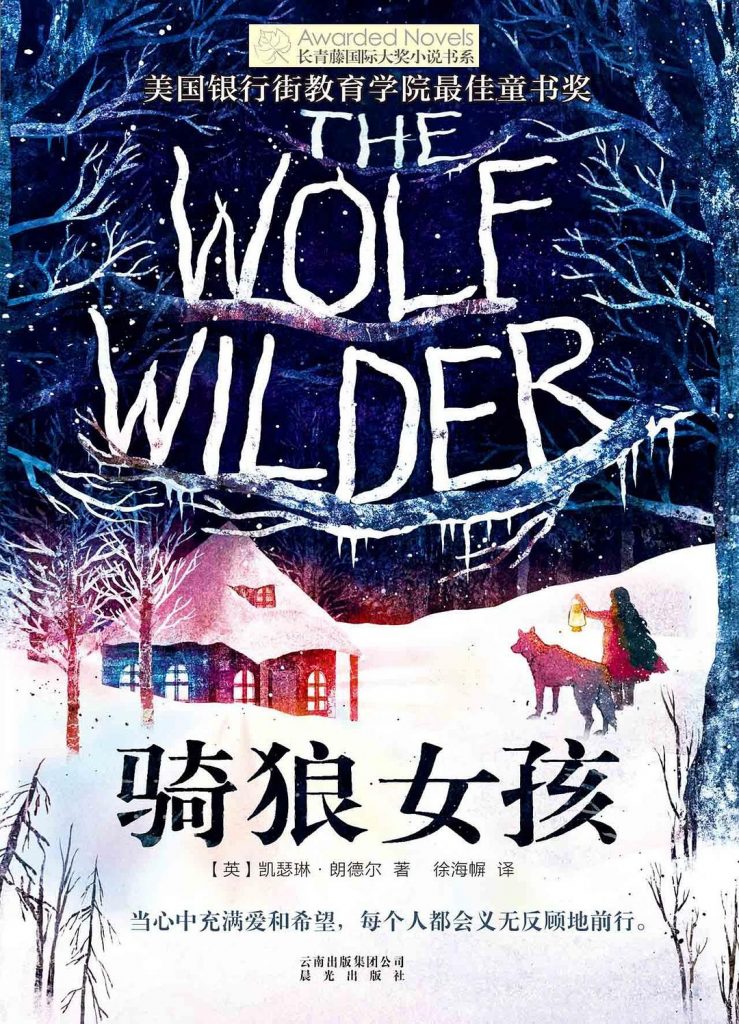
阅读和翻筋斗如出一辙:它们翻转世界,让你喘不过气来。
——凯萨琳·朗德尔
执高等教育牛耳的牛津学院体系里,有近600年历史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有“学术圣地”之称。这个学院没有大学部,全由研究生和教授组成。它九月的入学考试号称“全世界最难”,平均每年录取两个学生。
英国童书作家凯萨琳·朗德尔(Katherine Rundell , 1987-)21岁时考进了万灵学院,成了学院史上最年轻的女性成员,之后也在学院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这足以证明她是学霸中的学霸,被比喻成“当代女性托尔金”实至名归。
然而稍微了解朗德尔生平,就会发现她远非人们对传统学院派的刻板印象。她的童年在非洲南部津巴布韦度过,出门几步便虫鱼鸟兽环绕,七岁时一只小象的喷嚏打在她脸上,中午放学后赤脚爬树,跳进湖里游泳……这股“野劲”在她回到欧洲后仍持续着:她喜欢早起翻筋斗,宿舍里悬空拉着绳索——不是晾衣服用,而是兴致来时能上去走索。在无山可爬的牛津,她夜里偷攀上古老建筑的屋顶天台,奖赏自己不一样的视野。近年她在纽约上过空中飞人课,进度缓慢地学开小飞机。所有这些远离书桌,远离图书馆的经历,与她的学术力道冲撞融合,喷洒出朗德尔独一无二的文字水花,溅落在她为孩子写的一页页小说里。
自幼喜爱阅读的我,随着岁月加添,读的作品增多,渐感大部分作品欠缺新意,甚至偶尔感到倦怠——传道书那句“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不时闯入昏倦脑海。发现朗德尔,如同被清凉水花泼醒。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故事场景跨越世界和历史的不同角落,也在乎她的叙述和比喻。“她以新鲜方式连结读者,她抓住我们的手腕,把我们从舒适躺椅上拉起来到户外,让我们和星光,和野外的刺鼻气味面对面。”
下面以发表顺序先来认识朗德尔的故事:
《野姑娘》(The Girl Savage, 2011/Cartwheeling in Thunderstorm,2014,美国版)
出生就被非洲阳光、雨露和动物环绕的薇儿,因双亲接连病逝,被送到伦敦寄宿学校。故事前半场景的津巴布韦和后半的伦敦仿佛两个世界。薇儿曾在阳光下红土地上自由翻滚、骑马奔驰,现在必须面对学业压力、同侪排挤霸凌,她学着在寒风厉雨里翻筋斗,在条条框框中突破自己。这是朗德尔的第一本小说,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编辑拿到初稿时一口气读完,“好像肺中灌满了清新的风”。即便在国际化的21世纪,大部分西方读者对非洲这块土地仍是陌生甚至带有偏见的,但打开《野姑娘》,几句话工夫就被薇儿这个野得酣畅淋漓的孩子彻底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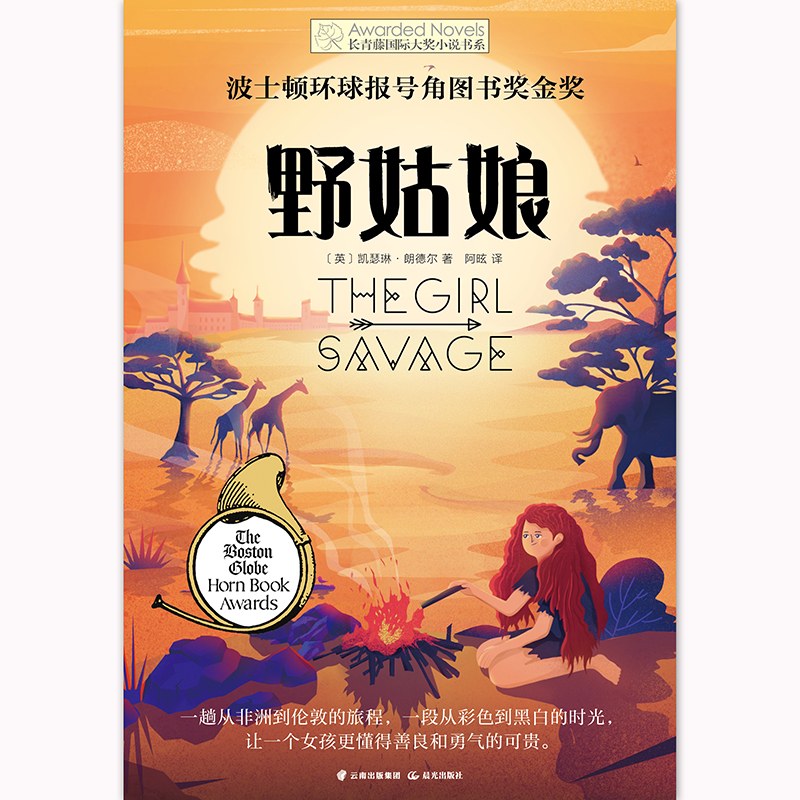
《屋顶上的索菲》(Rooftoppers, 2013)
在船难里获救,被特立独行的单身学者抚养大的女婴索菲,凭着一丝线索,越过英伦海峡到巴黎寻找生母。在这个故事里,朗德尔建构了一个不寻常的场景——巴黎屋顶上的世界,生动描绘了一群生活在屋顶和树上的孤儿。为什么他们协力帮助素昧平生的索菲?或许因为他们也像索菲一样,对有一天能找到母亲或父亲,有着不合逻辑的盼望。
《驯狼女孩》(The Wolf Wilder, 2015,又译《骑狼女孩》)
在西伯利亚北地,菲奥和妈妈接收俄罗斯贵族无法继续饲养的狼,训练它们恢复野性,拥有独立生存能力,帮助它们重回自然。母亲因抗拒沙皇麾下将军而被关进牢里,家园在烈焰中化为乌有,菲奥和狼群必须逃离现场。母亲叮嘱她向南逃到莫斯科,然而菲奥却选择留在苦寒北地。接下来不仅是生存考验,她还得决定是否接纳盟友?如何一步步开展成功希望渺茫的圣彼得堡监狱营救行动?菲奥和几只狼的友情让人泪下,而她与伙伴们展现的机智和勇气也让人震惊,证实了她母亲说过的那句话:“现在就是你最顽强的时候。孩子是世上最坚强的生物,他们无比坚韧。”
《大冒险家》(The Explorer, 2017,又译《荒野飞行》)
小飞机载着四个孩子飞越亚马逊丛林时,飞行员猝死,飞机一头栽进莽林。弗雷、小康和莱拉、麦斯两对姊弟奇迹般生还,如何脱困变成每一天的难题。陷在毫无人烟的丛林里,他们克服歧见,努力存活,梦想能重回文明,和家人团聚。他们偶然发现了标记着X的地图,随着地图进入隐藏在丛林深处的古老城市,遇到独自住在那里的神秘人物。神秘客掌握了他们重回文明的钥匙,但他开出的条件让弗雷难以接受……这个故事不仅是危机四伏的原始雨林探险之旅,也是深入内心丛林——面对恐惧、疑惑、憧憬、责任——的探险之旅。
《好小偷》(The Good Thieves, 2019,又译《义贼》)
1930年代的纽约,黑手党猖狂,平民百姓争相自保。为了帮助才丧偶的外公讨回被黑帮诈骗走的家产,尤其是那条象征外公外婆几十年爱情的绿宝石项链,12岁的薇塔立誓组成对抗恶棍的团队,执行秘密义贼任务。队伍不可思议地梦幻:飞刀手、空中飞人、驯兽师、神偷,也不可思议地年轻。这些十来岁孩子为着正义愿意挺身而出,尽管没有任何保证能全身而退。
朗德尔的小说地理位置跨越了世界各洲,场景包括都会和蛮荒,时代从百年前到现今。这些表面多元的故事其实有共通点:
爱是强大动机
朗德尔的故事推进通常和主人翁要寻回或救援至亲密切相关。《屋顶上的索菲》中主角紧握一缕线索——寻找生母,《驯狼女孩》中菲奥从西伯利亚荒原直闯圣彼得堡监狱援救母亲,《大冒险家》里深陷丛林孩子们的求生动力是回到家人怀抱,《好小偷》中义贼成军为薇塔外公讨回公道;即便在处女作《野姑娘》中,薇儿父母已经病逝,爸爸生前教会她的技能和品格,仍是她孤零零面对异地风雨,不失去对阳光盼望的主因。
当为孩子遮风避雨的成人陷入困境甚至绝境,对至亲顽强的爱,激发了孩子的创意、勇气与能力。如同薇塔对自己说的:“她一定得做点什么,让情况好转起来。她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然而爱正是如此——在爱面前,我们别无选择。”
一“群”孩子得胜
朗德尔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玄学派神职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多恩有句名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自全。”而朗德尔的故事里,再怎么厉害的少年主人翁都有更厉害的团队一起奋斗,团队情谊不受肤色、背景、个性,甚至物种的限制。这些盟友有的是危机开头就兴冲冲加入,也有人犹豫再三才入团,但无论先后,他们对彼此都有着让成人汗颜的忠诚,还有他们个人的天赋才能在团队里美丽结合(《大冒险家》里原本似乎只会哭的五岁鼻涕虫麦斯都被证明不可或缺),成就了这些故事的亮点。
惧怕中的勇气
朗德尔小说里的主人翁常于极端情境中,面对哥利亚级的对手,完成极端任务。孩子们在胆战心惊中匍匐前进,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愚勇,而是对至亲的爱在惧怕里撑着他们走下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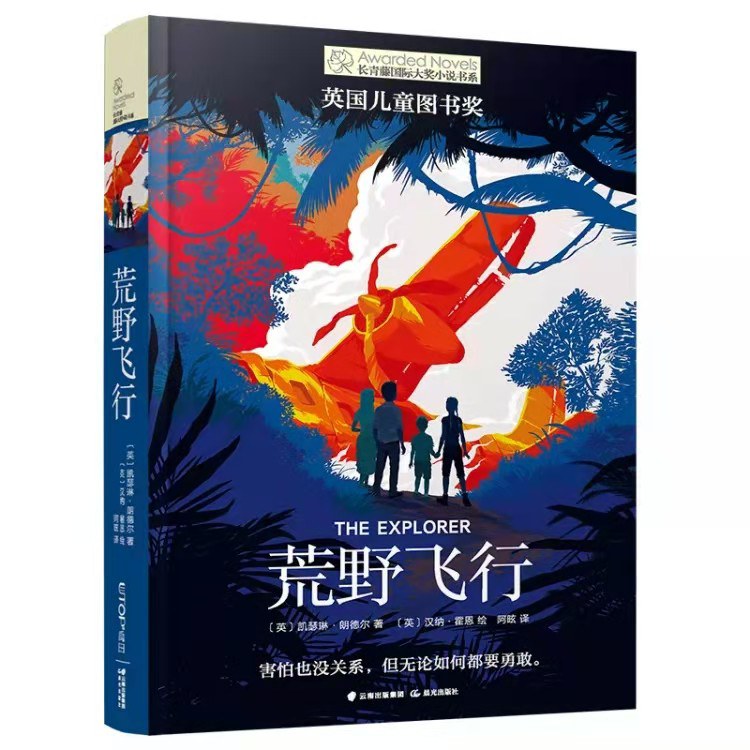
谈到勇气的来源,朗德尔如此解释:“我不知道勇气究竟打哪里来,但我知道只要能先凑出一丁点,更多的勇气会接续涌来。所以你不需要大量,只要一丝勇气就行。”面对随着排山倒海的黑暗而来的惧怕,孩子从哪里召唤一丝一毫的勇气?又如何不掉落勇敢?这个过程,是朗德尔角色成长的亮点。
自然从不缺席
伊甸园是人类第一个家园,亚当命名了各种活物,可是现代人与自然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往往想到相对低度开发的非洲,就想到落后、野蛮、炽热、动物间的弱肉强食。
但郎德尔在津巴布韦度过童少岁月,日夜浸泡在自然里,和许多昆虫、动物有第一手互动经验。她的笔杆下有动物皮毛纹路,墨汁里有草香泥土味,笔下的非洲、南美洲,甚至伦敦动物园都灿亮生辉,字里行间满溢对动植物和大自然的切切疼惜。受西方菁英教育,年纪轻轻就拿到学术象牙塔钥匙,朗德尔以她文明淬炼的精准语言和知识,谱写对自然野外的颂歌。
“关注”值得关注
多年研究诗人多恩,最触动朗德尔的是多恩虽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但到老年时仍坚持信仰,对生命依然有大写的赞叹和关注。而我在朗德尔的叙事里也反复读到她的深层关怀。2024年9月,她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说:“虽然世界混乱又烽火四起,但它的美丽、慷慨和错综复杂值得我们惊叹。世界如此庞大,不向其致敬是想象力、认知力和智慧的失败……所以我希望我的书传递这样的信息:‘注意!你欠缺对世界的关注,你欠缺对世界的爱。’”
小结
阅读朗德尔,我重拾遗失的开卷喜悦,笑声擦亮思考的火苗:天真烂漫的少年在遇到患难、艰苦、黑暗、挫折、失望……时,还能保持初心吗?现代人,包括我自己,对“野”的拒斥和对文明的拥抱不能并存吗?
小时候天天在屋外玩耍到日落,被昵称为“野马”的我,二年级时接触到课外书,加上大环境联考压力,不经意转变成了书虫和师长称赞的“文明”好学生。郎德尔的生活和创作却让我见识到,学霸和野孩子可能并存,并且正是这样的张力让她的故事有了不流俗的精彩!
《野姑娘》开场这么描述:
几年前,农场的一个客人曾问过薇儿关于窗户的问题。
“你爸爸肯定买得起一块玻璃吧?”
“我就喜欢灰扑扑的,”她这么回答,“还有湿哒哒的。”尘土和雨混合成泥巴,而泥巴充满无限的可能。
窗户是一块工厂制造的玻璃,今天的孩子和成人终日面对的荧幕也是一块块由工厂制造的玻璃,玻璃有它的便利和功用,但是否也让我们失去某些难以取代的事物?
朗德尔笔下的薇儿选择窗户不装玻璃,让阳光、雨水、尘埃、虫子自由落下;朗德尔的故事也欢迎没有玻璃的窗,不落栓的门,营火边烤焦鲜香的蜘蛛,安睡在教堂圣像边的野狼,屋顶上把安魂曲拉成生命礼赞的大提琴手。她的作品深度来自于少年面对的难题真实、没有单纯迅速的解方。他们的希望来自,风雨长夜后的世界还是有闪闪发光的露珠——微小、短暂、晶亮。
在这些故事里,天上有灿烂阳光,而地上露珠反映的微光同样让人惊奇敬畏——只要眼光够专注,并且带着爱。
作者簡介

黄瑞怡
台湾大学图书馆学学士,美国俄亥俄州大学语文教育博士,专攻儿童青少年文学。多年在南加公私立中小学任职,现任联合基督教学校国际学生部主任,创世纪文字培训书苑资深同工。《飞扬》杂志2011年征文比赛首奖。著有《艺出造化意本自然——杨志成的创作世界》。台湾《校园杂志》“尴尬少年游”,“恶水筑书桥”专栏作者。曾参与远东广播公司童话系列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