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此我说
- 08/19/2025
【时评】刘嘉:指尖上的暴力,为何让一个人坠楼?
作者:刘嘉
当我们看一个人,是只看他的立场、阵营、过错,还是承认他是一个有尊严、有复杂情感的生命?愿自有永有者引导我们以行动作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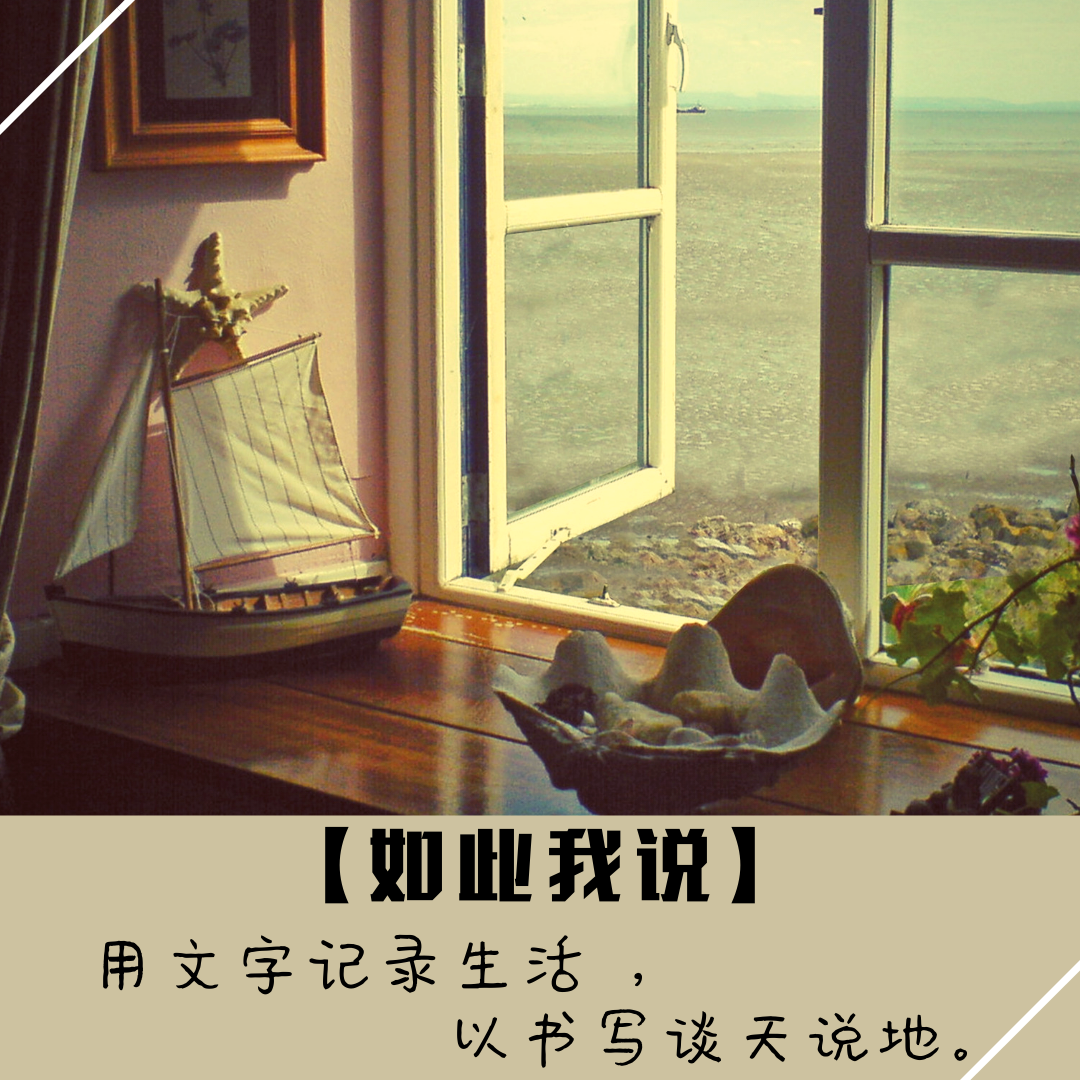

近日,河南周口的一个新闻,让无数人唏嘘不已——一名妇产科医生,从楼上坠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家属说,长期的网络暴力,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三起医疗纠纷引发的舆论漩涡,把她推到公众的审判台上。有人在网上指责,有人恶语相向,还有人把侮辱性的词汇反复挂在她名字后面。
在短视频平台,她的工作场景被剪辑、拼接成情绪化的内容,评论区成了集体宣泄的出口。她的朋友圈和社交平台成了舆论的靶心,熟人和陌生人混杂在同一个骂声合唱里。调查组已经介入,具体责任还在查。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无法回避:一个人,在数不清的指责与辱骂声中,孤立无援地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这不是第一起网暴死亡事件。过去几年,从娱乐圈演员到普通的老师、护士,甚至中学生,类似悲剧屡屡出现。每一次,我们都震惊、愤慨、呼吁改变,但热度过去,一切又回到原点。下一次悲剧来时,人们仍说:怎么又发生了?
但现实是,这个问题并不会自己消失。网络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空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既是潜在受害者,也可能是无意中的施暴者。按下回车键的手指,能救人,也能杀人。
为什么网络时代更容易网暴?
网络时代的信息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我们的注意力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大多数人不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遭遇停下来了解全貌,只会在短暂时间内做出判断。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去个体化效应”。人在群体中容易丧失自我约束感,而网络正是一个巨大的匿名人群。当你觉得“大家都在骂”,你就更容易参与其中,因为有一种“正义群众”的错觉。
更糟的是,算法机制会推送同类观点,让你以为“全世界都和我一样愤怒”,从而进一步加剧攻击性。这就像在封闭的回音室里,你只听到自己喜欢听的声音,直到它变成咆哮。于是,网暴就这样形成了:一则未经完全核实的信息,配上夸张的标题和断章取义的视频,再加上评论区的情绪引导,很快,一个人就会被推到舆论的绞刑架上,任人投掷石头。
网暴的根本是看不见“人”
很多人以为,网络暴力就是骂人。但它的根本,不只是骂,而是语言的暴力化。语言的暴力,有几个显著特征:第一,夸张化。为了吸引注意力,情绪和措辞都会被推到极端。一次医疗差错,被说成“草菅人命”;一次服务不到位,直接升级为“丧尽天良”。夸张一旦成了语言上的暴力,它就会用情绪压过事实,让理性退到角落。
第二,标签化。给人贴上一个负面标签,然后用标签替代整个人。比如“黑心医生”“骗子”“人渣”,这些词一旦落下,就像刻印,任你怎么解释都难以抹掉。
第三,去人化。当我们攻击一个陌生人时,我们往往不再把他当“人”看,而是当作一个靶子,一个虚拟的符号。这样一来,语言就不再有分寸,因为我们已经把对方从“有血有肉的生命”降格为“发泄对象”。
法国记者让·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在《砍刀的季节》(Machete Season)一书中,记录了多位参与卢旺达大屠杀者的口述。其中有一名男子,亲手杀死了与自己为邻多年的朋友。他回忆说:“在那致命的一刻,我没有看见他曾经的模样。”就在砍刀落下的前一秒,邻居的面孔在他眼里变得模糊,“五官的轮廓确实与我认识的那个人相似,但我的脑海中,没有任何清晰的念头告诉我,我们曾相邻而居那么多年。”那一瞬间,邻居在最真实的意义上,“看不见”了。那是一种心理上的失明。当你不再把对方当人看,任何伤害都变得理所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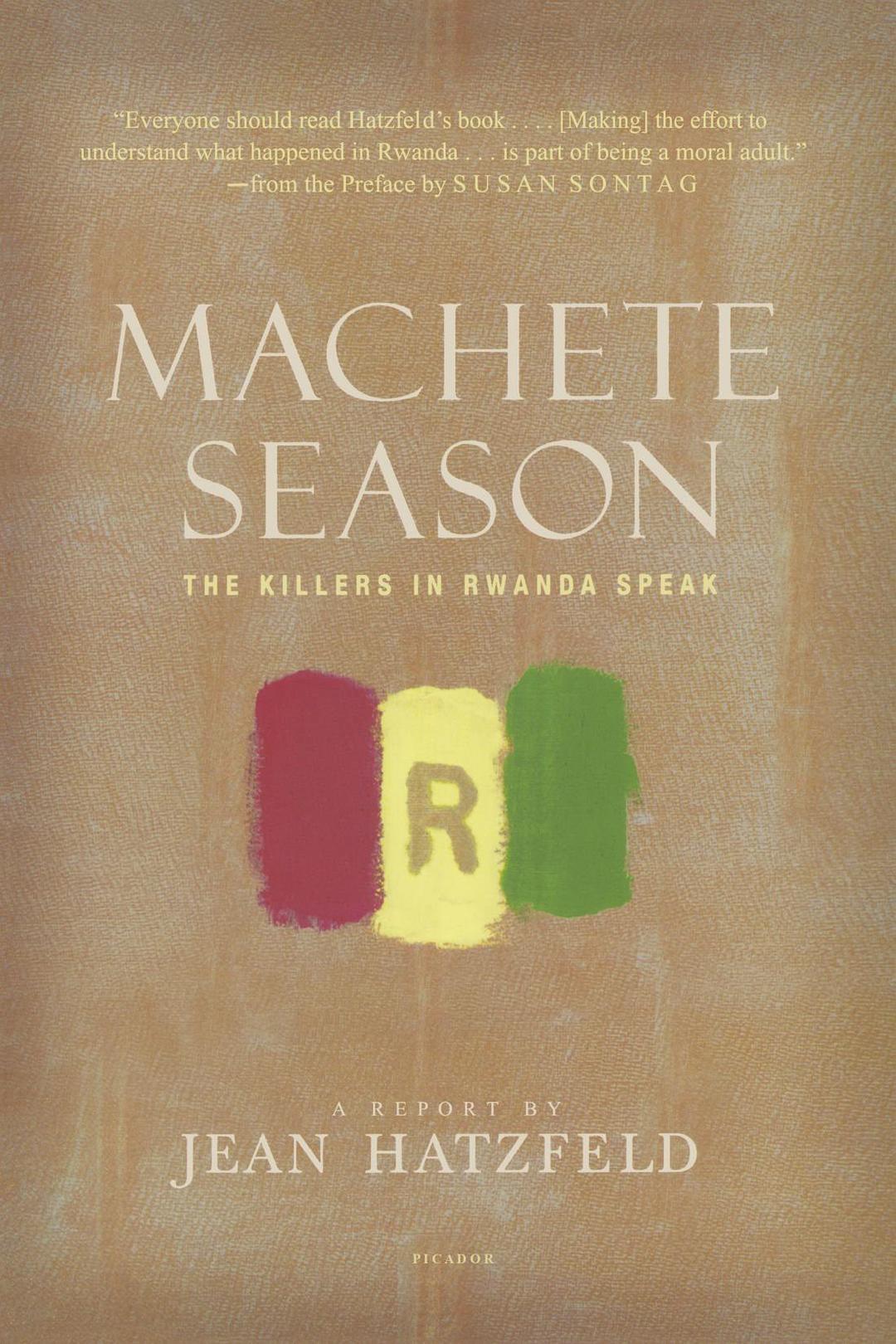
我越来越觉得,网络暴力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失去了“看见人”的能力。哲学家伊里斯·默多克曾说,道德生活的核心,不在重大抉择的时刻,而在日常细节中你如何去“看”别人。当我们真正看见一个人时,不是只看到他的标签、身份、过错,而是承认他是一个有尊严、有复杂情感的生命。
但现实是,我们更容易看见的,是“立场”“阵营”“群体身份”。当人被简化为一种身份或标签,他就不再是完整的“人”,只是一个“代表”,一个可以被攻击的符号。于是,当我们对着头像开火时,不会感到愧疚,因为那好像不是一个会受伤的人。这种“看不见”,不只发生在网络上,也发生在地铁里、餐馆里、办公室里。当我们对清洁工、快递员、服务员冷眼相对时,我们也是在忽略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爱人如己,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操练,当你在生活中真正遇到另一个人时,你要放下成见,用耐心和分辨力去看他。这种“看见”,可以很细微:在上网评论前,先问自己:“我看到的是全部事实吗?”当身边人情绪失落时,留意到他的沉默,轻声问一句:“你还好吗?”在公共争论里,试着先去理解对方的处境,而不是急着反驳。
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
这种看见,需要刻意练习。治疗师兼作家玛丽·派弗(Mary Pipher)受过专业训练,但她在心理治疗中的“诀窍”恰恰是——没有诀窍,只是与来访者真诚地展开对话。她认为,作为治疗师,最重要的不是急于给出解决方案,而是那份“关注的方式——这正是爱最纯粹的形式”。正如她在《给年轻心理师的27封信》中所写:“在治疗中,正如在生活中,视角就是一切。”
派弗在实践中展现出一种愉悦而清醒的现实主义。在她的领域里,许多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往往相信人类被黑暗的本能、压抑与竞争欲驱动;而玛丽这位曾当过餐厅服务员的治疗师,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些脆弱、渴望被爱的个体,只是偶尔被困在糟糕的处境中。她总是努力走进每个人的视角,以充满怜悯的目光去看待他们,把他们当作正在竭尽全力生活的人。她的根本立场很简单,也很坚定:对所有人怀有怜悯之心。
圣书里有一句话:“祂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祂在人群中,总是先看见他们真实的需要:饥饿的得饱足,病痛的得医治,迷失的被引回正路。祂的怜悯不仅是情感的触动,更是化为行动的爱。有一位牧者,在看见任何一个人时,会想到那是按着创造者形象被造的生命。在他眼中,每一张面孔,都多少映着创造者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是拥有永恒灵魂的受造物,是具备无限价值与尊严的存在。每当迎接一个人,他都在努力回应信仰的呼召:用主的眼光去看人。那是一种怜悯、温柔、尊重的目光,尤其会停留在那些卑微的、被忽略的、受伤的生命身上。对他而言,世上没有一个人微不足道——每一位他遇见的人,都宝贵到值得主为之舍命。
指尖上的选择
无论是舌头的暴力,还是指尖上的暴力,都是由心发出。如箴言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因此,我们每天都需要保守自己的心——尤其是在指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C.S.路易斯说:“不存在普通人,我们嬉笑、公事、结婚、冷落、剥削的对象都是不朽的人,要么不朽地恐怖,要么永恒地辉耀。”在网络时代,我们的手指每天都在做选择:是用它去理解、安慰、帮助,还是去攻击、讥讽、推别人走向绝境?这一击,可以是一个“赞”,也可以是一句诅咒;可以是伸出去的手,也可以是推下去的力。指尖上的暴力,会让人坠楼;但指尖上的善意,也能让人重新站起来。
在信息的洪流里,我们无法一次救所有人,但我们可以一次少伤害一个人。这就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也是每个键盘前的人必须守住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