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人却依旧是人。当祂站在一个人面前的时候,要多沉的重量,才能把这个人拖慢下来,以至于他没有转身走开的力气,也有停留倾听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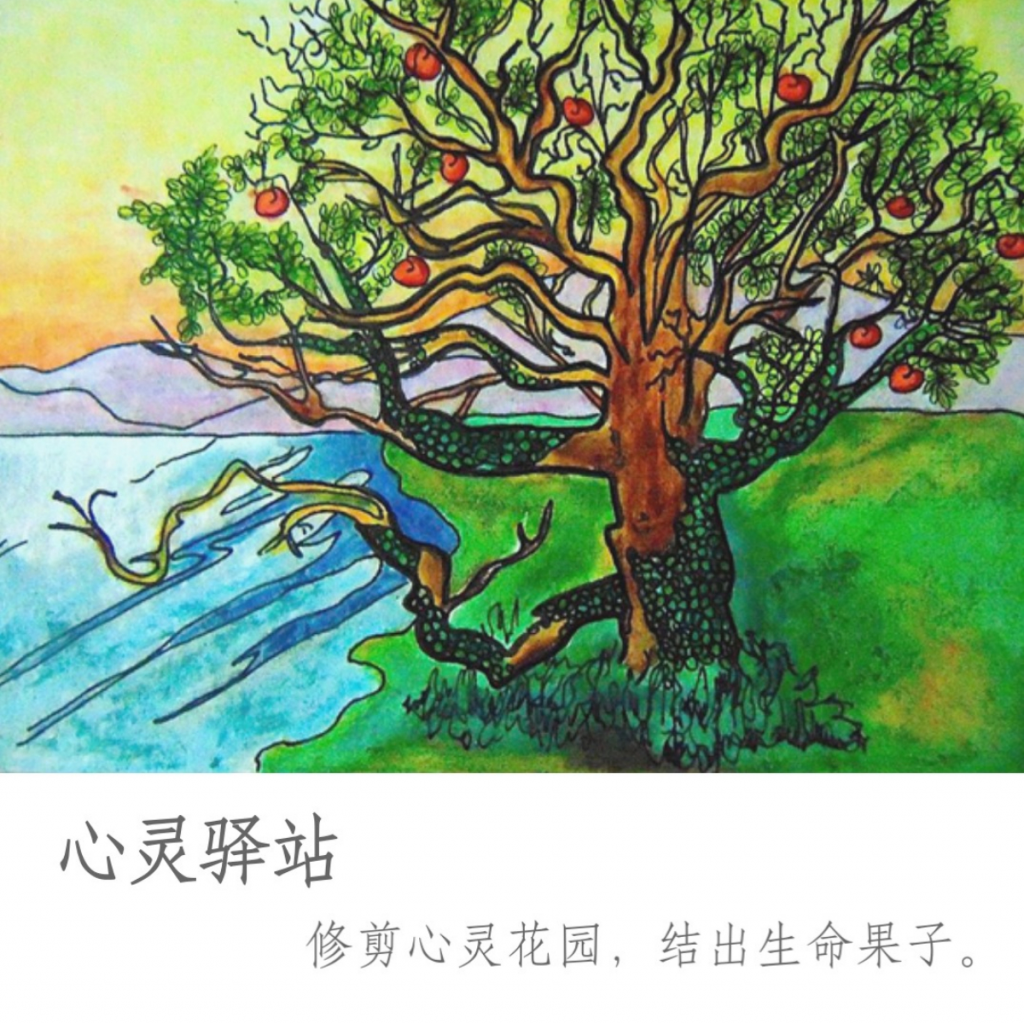
几年前,有位活泼风趣的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谈到撒玛利亚妇人到井边取水,说:“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时代,她要取的该是咖啡了!”牧师生活在高节奏、压力大,同时又是抑郁高发的纽约,早晨一杯咖啡,是许多人的精力之源、起床之药——要说它是“生命之水”,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为过。
时代变迁,从撒玛利亚烈日下的井边到纽约早餐店里的咖啡机旁,人依旧是人。那口千年前的井,已在时光的流逝下改换了形状、质地、气味,然而它的功能忠实如昨。在井口辘轳的咿呀声里,或是咖啡粉被热水快速浸过时发出的吱吱响动中,等待的人双脚不安地改换姿势,仿佛有一点不耐烦;又或许全然没有想那么多,她只是在简单地期待着下一分钟,从终于到手的容器里畅饮一大口,满足身体最直接也最单纯的需要。
在这种单纯的期待里,她、我或者你,突然听到耶稣说:你想要生命的活水吗?
我突然开始忧虑,纽约清晨的早餐店里,作为一位已经付钱、正在排队、五分钟后就得离开赶地铁去上班的妇人,也许我会轻快地对耶稣说:谢谢,不过我现在没有时间交谈。

两千年前,在各种地点、时间、场合,耶稣或许也曾被形形色色的人,如此拒绝去开始一场交谈。或许他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又或许在不久或许久后的将来,憾恨到顿足捶胸?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没有机会留下如约翰福音第四章中那样,流传后世千年的故事。
在那口井边的妇人,她不急着奔赴自己行事历中的下一站。或许,她本就计划用这汲水的时间,消停休息一会儿。或许,当她挑着、顶着或扛着水罐来到井边的时候,已经因着身上的重量,而拖着脚了。
要多沉的重量,才能终于把一个人拖到慢下来呢?沉重到,当耶稣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行事历已经被那重量压毁了,以至于她没有转身走开的力气,也有停留倾听的自由?
十五年前,我发现自己不再赶着去上下一节课、做下一套题、为下一场考试刷夜了,在自己的行事历被抑郁压毁以后。那时,我终于看见了站在我跟前的耶稣。
那位井边的妇人,她大概不抑郁,甚至是活泼热情的也说不定。她有心力在五段婚姻失败以后,还与第六个男朋友经营感情。这种屡败屡战的精神与意志,令我自愧不如,感慨万千。
耶稣没有凭着她的丰富感情史就定她的罪。且看,祂给了她赞许与肯定:她没有说谎,她说出来的是真相的一部分;同时她选择透露的这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真相。她没有透露全部的真相,这也并没有招来祂的斥责。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对自己的保护。即使在我们当今开放的社会里,一个因着无论离婚,还是丧偶,一共失去过五次伴侣的人,在听到原因为何之前,有多少人已经戴上有色眼镜去看待呢?

无论犯罪与否,来自邻舍的冷眼,加上五段不得善终的婚姻,这一切在一个人心中所能投下的心理阴影——让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完全不是只要打好手上这一桶水,然后就万事大吉的啊!在突然有了一个机会面对耶稣的时候,她已经清楚,自己是一位从身到心,都大有需要的人。这种对自己的清楚认识,让她不拘于“打一桶水”这个就事论事的任务安排,而是在耶稣面前停下来,认真审视祂,也面对自己。
她看得见自己里面有一个空洞,这空洞也给了她与耶稣坐而论道的思维空间。于是,当耶稣的提议——“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听起来有一点思维发散,她的回应——“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神,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听起来也有一点跳脱。或许当年的耶稣听得此言,会微笑起来吧。
两千年后,当年的撒玛利亚村落早作过眼云烟,那一口井边的沃野也沦为了民族相争的战场,却有一小群人站在天边的云端:其中,有着当年那位容貌可人,而际遇多舛,却被一杯水永远改变命运的女子;也有着与她同村的邻里乡亲,他们听了她的广而告之,而相携出门看耶稣,结果大家都因着信弥赛亚而拥有了永远的生命。历史不断翻页,而他们的灵魂不朽,和古往今来其他众多的信者一起,站在荣耀的云里,与天父一同注视着当今的世界。
在春寒料峭的纽约街头,当我裹紧了大衣、拖着脚步走往咖啡店的时候,头顶一块又大又透明的云彩里,有一双又黑又亮、眼窝深而睫毛长的眼睛,正向我投以鼓励的眼神,无声地呐喊着加油的词句。(希伯来书12:1)
—THE END—
作者简介
伊零
又名一泠,年四十,现居北美。十六年前,道心破碎,然后被主捡起一地的碎片。余生是一场与祂同路的旅行,兜兜转转、停停走走、且行且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