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儿夫妇成长的过程,颠覆了两句话:一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二概括为“妈宝男不值得托付”。他们的婚姻怎样走入了春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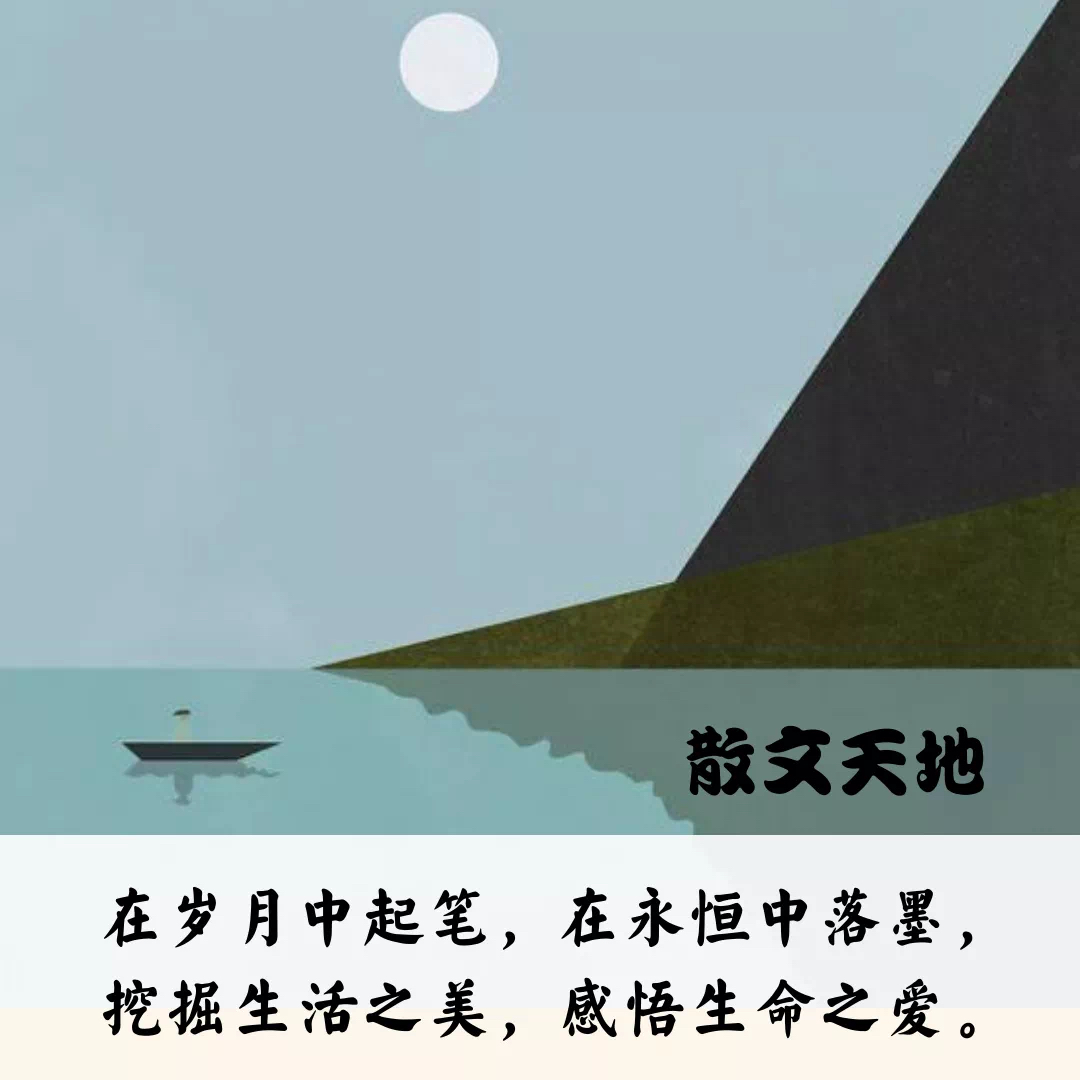
爱人姓牛,平时我都叫他“牛”(后文的“牛”都是指爱人)。我和牛认识23年,结婚22年,从少不更事到现在学习扶持,经历许多风风雨雨。
我们是2001年经人介绍认识的。当时我刚到他们村小学教书。他母亲想为他找一个教师做媳妇,就常常到学校小卖部转悠。后来经小卖部老板娘介绍认识校长妻子,校长妻子就把我介绍给她。婆婆从小卖部观察我之后,同意介绍给儿子。
当天晚上,我和牛在校长办公室见面。他肤白帅气,留着一缕小胡子,显得既文气又有几分机灵。我对他一见钟情。落座后我们开始聊天,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校长妻子有点不耐烦,不断进来暗示我们。两个傻帽愣是没发现,等人家开始不时打断我们,我们才意识到该离开了。
接下来是一个星期的沉默。我坐卧不安。一天晚上,我和舍友(同住校的老师)聊到爱情话题。我说起牛的沉默,舍友脱口而出:“去找他,问个清楚。”我干脆回应:“好!”舍友只是说说而已,但看到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穿衣服,才知道我是认真的。
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我们两人都没骑车,步行到他单位需要两个小时。同事很仗义,愿意陪我前往。到达牛单位已经11点多,又在传达室等到凌晨两点半,他才从车间出来。看到我们,他很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

当时我不知道他正经历一场恋爱,据他讲那女孩又高又瘦,还很漂亮,但因为她已订婚,婆婆和姐姐都不同意他们交往。那女孩结婚时,他去参加她的婚礼,在婚宴上豪饮。这是很多年后牛告诉我的。幸亏当时我一无所知,否则我很可能没有勇气去单位找他。
很快我们订婚了。他每天下班都到学校找我,坐在炉子旁边,手握一杯白开水,小口小口呷着,坐到很晚才离开。我迷恋这种宁静而安然的交往,每天都期待傍晚快快到来。
半年后,我们结婚了。他21岁,我23岁。
结婚当天下着瓢泼大雨。他家门前是土路,地势很低,小汽车无法进入巷子。我坐大巴到他家门前,感觉不像结婚,像串亲戚。等亲戚都下车后,车窗外是围观的人群和瓢泼的大雨,空空的大巴里只剩下我,在等待牛牵我的手去拜堂。
那一刻我陷入莫名的恐惧,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离我而去,而我知道它再也无法回来。眼前这个人和马上要进入的家庭,不足以让我感觉安全与满足。我大哭起来。
现在想想很可笑,人家都是笑着进入婚礼,我是哭着开始拜堂;人家婚宴时,穿的是新衣裳,我因为没心情,脱下婚纱后,穿的是旧衣裳。
在年轻的岁月中,我和牛都在寻求一个理想的灵魂伴侣,却都没把目光投在配偶身上。当我们的婚姻发生变故时,牛和婆婆的关系却特别好。公公常年在外,一年只回来几次,平时都是牛和婆婆在家。
婚后第一年,我们和婆婆住在一起。他们之间自然和谐,自成一体,我就像一个外人。我俩吵架时,这种感觉尤为明显。平时我们在东厢房住,婆婆在堂屋住。吵架的夜晚,他会离开我,住到堂屋。每次听到堂屋的铁栓落下的咔嗒声,我有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
我们的关系时好时坏。好时,两人一起散步聊天;不合,也大多因聊天而起。年轻的我们常常吵着要离婚。
2011年,我们真的离婚了。两个人笑盈盈地到民政局,拍照,办离婚证。当时工作人员认为我们是为了买第二套商品房,要办假离婚。我们约定夫妻做不成,要做最好的朋友。
可是,我刚回到学校,给他打电话,他就语气大变。一周后,我杀回家,接下来是一个多月的婚姻保卫战。后来我胜利了,可我们都精疲力竭,元气大伤。离婚时是开开心心去离婚,复婚时却是公事公办型。我们的关系依然是死的,他的冰冷让我无能为力。
那一段时间,我爱上骑行。每到周末,或晚上有活动,我都会尽力参加。在疯狂的行驶中,我得到一种快乐。身体虚脱,精神却得以满足。我拉上牛,让他跟我们一起骑,想激起他的热情,但他就像对读书和散步那样,没有兴趣。骑几次就会罢工,或者气呼呼地独自在前面骑,不理我们。

2012年5月我信主。祂把爱的面纱慢慢向我揭开。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爱: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付出与牺牲,爱不是占有。我察觉到自己对牛的感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占有。我开始慢慢学习爱牛,爱孩子;学习控制情绪,学习付出。
我的脾气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我常会愤怒到歇斯底里,不能自已,手机、电脑和电视机都摔过。可信主后,我再没摔过,倒是他开始摔起来。很有意思的是他只摔不值钱的。他质疑挖苦我的信仰,我努力吞下来;他不去教会,我带着儿子去。我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一年后,牛也决志信主,开始和我们一起去教会。
在团契生活中,我们的价值观开始趋同:学习到夫妻应该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学习到祂的关系次序是“神-配偶-孩子-父母”;学习到管教不是教训或惩罚,孩子需要陪伴、理解和接纳等。
我们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虽然还经常吵,但我不再那么绝望,会对沟通的失败有所反思。我意识到对牛,我不能操之过急,要拿掉我对他的理想标准,学习以祂的眼光来看他,接纳现在的他,耐心陪伴,等候他的成长。渐渐地,他竟然也开始反省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惰性,觉察到需要成长,并提出让我督促他。
同时,祂借着儿子的教育问题,迫使我们沟通。无数次失败,又无数次重来,直到可以平心静气地谈完一个话题。
我认识到对儿子的亏欠,开始花时间陪伴他,学习用祂的原则与他互动。儿子从初一一直到高四,共七年时间,和我同一所学校。他身上暴露出来的一个个问题,就像一团团小小的火焰,烧掉我在同事心中高冷和理想化的面纱。在学习管教儿子的过程中,我也学习开放自己,与人沟通,不怕呈现真实的自我。
牛对儿子的成长是手足无措的。他会带他一起玩游戏,但不会与他交流。玩起来他们像是兄弟,但当他想要树立父亲的威严时,他们马上会干起仗来。那时我的行为也不恰当,常被他们拉来充当裁判,而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儿子。这样就使情形恶化,牛越来越不管事,理直气壮地把教育儿子的责任推到我身上,儿子也不懂得尊重他。
这种情形直到2020年,我和爱人共读《磐石上的婚姻》这本书才有所改变。牛很不爱读书,那是他认识我之后第一本完整读完的书。读完之后的分享,简直就是他控诉我的机会。正是透过那一次次的“控诉”,我了解到他内心深处的委屈,了解到他的想法。我们的沟通也变得越来越具体,不再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命题和要求。
那时,儿子正值高三,情绪容易低沉,矛头容易指向我,因为我太看重他的成绩。每次要和儿子沟通,我就先怂恿老公出面。他有点害怕和儿子交流,总想退缩。我需要鼓励他,一步步和他商量如何应对:先预测儿子会说什么话,当他说这样的话时,你说什么;儿子说到什么程度,流露出什么情绪,你就不要再接招,退出来就好……这个交流过程,对我们夫妻的情感凝聚也很有帮助。
儿子高三高四的两年时光,我们三个人都很辛苦。我和牛并肩战斗,常会出现还没开始对外,我俩先斗翻了。不过特别感恩的是,我可以躲到祂的里面,得到修复后,再帮助他修复。而牛修复得越来越快,生闷气的时间越来越短。后来有些时候,竟然是我还在生气,他就不生气了。真是恩典!
更感恩的是祂所赐的二宝,对我们夫妻是极大的祝福。我们都不愿意让孩子看到充满怒气的父母形象。每次看到二宝害怕或疑惑的小脸,我们两个都会努力转换表情和语气。二宝有时会问:“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那么严肃(或生气)?”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说:“不是因为你,是我们自己遇到困难,需要解决。”孩子就会放下心来。

也是在不知不觉间,爱人慢慢从婆婆的语言行为和思维系统中抽离出来。这个过程对牛和婆婆都不容易。牛需要克服的是“孝顺”二字的桎梏,我需要一遍遍提醒他:“只有你离开一点,咱爸才能参与进来。”
婆婆拒绝和公公住在一起,我鼓励牛劝说婆婆,她和公公才是真正的一家,他们只有住在一起,关系才有可能慢慢建立起来。每次谈都不会太愉快,有一次她甚至哭着说:“咋了?我让儿子照顾我咋了?养他这么多年,不该吗?”
从2016年到现在,每年冬天公婆会有四五个月的时间住在我们家。婆婆对儿子的依恋和对公公的排斥,直到现在还有,不过我看到她也在改变:进我们的卧室前学会敲门;翻我们的衣柜前(或后),学会和我们打招呼;越来越少对我的购物和做家务能力给差评(但还会频繁给公公差评);有病时学习让公公照顾她,给她捏腿或穿衣服,而不是喊牛,把公公晾到一边。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把我拉过来,坐在她的床头,让我听她控诉公公和公公的母亲,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她说得很伤心,我听得也很难受。
不过这几个月中,婆婆有她的法宝:做好烙饼,母子俩坐在餐桌前,她看着牛吃。看牛吃得多,就高兴地说:“你看我孩儿,少吃点,我就怕你吃坏肚子。”四十多岁的先生,就像得到鼓励的小孩子一样,吃得更欢。那一刻我就觉得那个长大了一点的男人又退回去了。
莫非老师曾经在一篇信息中讲过,配偶有三个身份:爱人、父亲(母亲)和儿子(女儿)。作为妻子,我要帮助他成为这个家的脊梁,成为孩子的好父亲,可是也需要照顾到他做儿子的需要,否则他会不完整。如今我还做不到很好地照顾他,那就需要允许婆婆偶尔进来,帮助我照顾他心灵深处做儿子的那一份需求。直到有一天,我有能力照顾到他的那一份需要,就会满足他对母性的渴求。
可是,每到这时候,我也会找机会对牛“普法”:你是我丈夫,要和我共同照顾这个家,我当然会对你有所要求,会要求你挑起重担;我有工作,你不能期待我像妈妈一样全方位地照顾你。
我讲这些话,他虽然不太乐意听,有时候会嘴角撇撇,但还是会理解,并且愿意慢慢走出舒适区,努力做我的丈夫和家里的头。牛儿夫妇成长的过程,颠覆了两句话:一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二是“妈宝百分之六十,妻子会很痛苦;妈宝如果达到百分之八十,我建议妻子离婚”(国内一位很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所言)。
这两句话在无神论的世界基本成立,可是在有祂的地方却站不住脚。曾经,牛和婆婆简直就是一体的,几乎是不可分割的,可是因为祂的介入,牛逐渐离开母亲,和我成为一体。牛和我的性情都改变了,我们的婚姻还持续着,而且能够成为对方强大的支持系统。
我相信牛儿夫妇的后半生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