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中处处有等待,被动等待,也主动等待。作者说,在等待中,将自己倒空,而后真正活过来。你认为等待是什么呢?有意义吗?

外卖排起了长龙,狭窄的走廊里挤满了人,大片的口罩裸露着无处安放的双眼。当表情被遮住一半,身体语言在密闭的空间里被无形放大,低头滑手机的迅速,左右脚的支撑站立不停交叉,口中刺耳不耐烦的“啧啧”声。
四零三、四零四……外卖号都排到三位数字,但你并不知道这号码意味着前面有数百人已经和你经历过同样的等待,还是,这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数字,赋予它真实意义的,是你手里拿到热辣辣包装盒的那一刻。
这是下班后的疲倦晚八点。这是分布香港七百万人横七竖八、密密匝匝街区中的一点。这样的时空交汇,却在此刻充斥了整个世界,压在坐在一排长椅中尚逼仄等待的我身上。
不断有新人向里涌进,或者是我感到有千军万马正在我面前闪过,他们是阻止我与目标相会的敌军,是他们让我无法立即拎起外卖,飞奔回家。一天忙乱工作后的情绪感受,正在此刻慢慢袭来,连同眼前的噪杂,迫近口罩的勒紧,要将我压缩成一个很小很小的点,直等小到无极限后,再瞬间爆发宇宙。
这是等待的嘲弄。即使如此微薄的时间碎片,却是全然的被动与无力。等外卖,等下一班地铁,等超市结账,等手机消息弹出,等天亮,等口罩摘下顺畅呼吸的时刻……一天有多少时间在如此碎片中无力踱步,试图拼凑难以辨认的完全图景。
这个世界裹挟着我,正缓慢进入一个等待的季节。
像是高速旋转的陀螺逐渐失去外力,人开始往里退,先将口鼻捂紧,再关上门窗,最后退到内室。空气中不可见的病毒成了可见的屏障,绝对模糊的信号带来绝对恐惧的瘫倒。

等待由最初自信以为的数月,再到怀疑支吾的经年;从疯抢口罩的恐慌,到选购琳琅口罩的“新时尚”;从试图恢复“正常”,到重新定义“正常”。没有什么不在颠覆——明明被迫,却缓慢得让人无法察觉其荒谬性。心中希冀的,全压在未来未知的等待中。
但人太不擅长等待,所以在感到内心某些东西流逝的过程中,一定要用之制造些什么,生出些什么,挣扎着不肯让它死去,不肯放弃自己的以为。当人与人之间的外部交流被迫切断,内心对孤独的反抗将之转向虚拟世界,转至同室的亲近之人,各自为营,操戈相向。
人们在屏幕的光亮与内室的黑暗之间来回穿梭,在内心的伤痕与键盘的尖叫中撕扯恨意,在渴望被爱的自我与无力给予的他人中博弈消耗。等待的碎片被随时随地的信息碎片充斥着,叫嚣着,争夺着,将心碰撞着散乱,又悬浮着无法降落。
的确,最恐惧的是无意义、被流放,如同加缪在《SHU YI》中描述人们不可预知的生活状态——“对现时丧失耐心,又敌视过去,放弃未来,活似受人世间法律或仇恨的制裁,过着铁窗生活的人”。
于是,等待的无着落成了最广阔无边的牢笼,它可以自由漂浮,却无时无刻不指向内心深深的怀疑:如果煎熬苦难,到头来只是苦难本身,一切归于黑暗与空无,那人生究竟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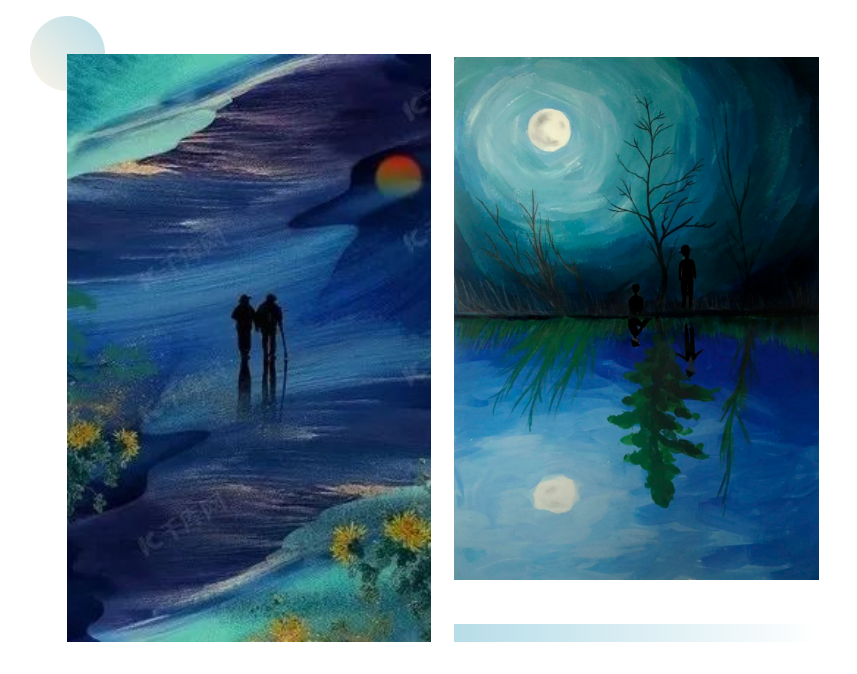
等待成了对抗无力感——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不知定期的无力感。在寂静的、空无一人的时候,对抗心底生出的冲动——一定要做些什么,证明不是在白白消耗,证明此时的无力仍有意义。我知道,是我难以面对赤身露体的自己,什么都不做的自己,拒绝听到心底最深处的声音,害怕听到那声音说:你是没用的、没人要的、被人遗忘的。
最无力的等待,也在写作的空白中成了刺骨的荆丛,将本是最自由的释放,生生长成最想挣脱的禁锢。曾经忙碌的时间里激情满满,感到胸中有无数言词想要吐露,不同思想在我脑中碰撞激荡。只是生活连轴转时,总告诉自己时间不够,等到“闲暇”时再写无妨。
然而,我忘了闲暇并非一种理想状态,它的到来固然有平静安慰,却也掺杂着太多的未知焦虑和自我定罪。当我真正走到这一步时,发现自己竟已无话可说,有的只是无尽的情感挣扎。从前想要叙述的、我以为的真理,在如今灵里的混沌中,只剩一遍又一遍重复的、近乎哀求的祷告:“告诉我你在,你依然在。”
等待拖成了最苍白的叙述,空荡的页面停留在第一个光标闪烁里。焦虑良久,仍无法打出一个字,刺眼得让我无数次关掉文档,抗拒坐在计算机前。当我感到自己枯竭得无法再给出,当我连自己的感受都无法看清时,我是否能够写出打动人心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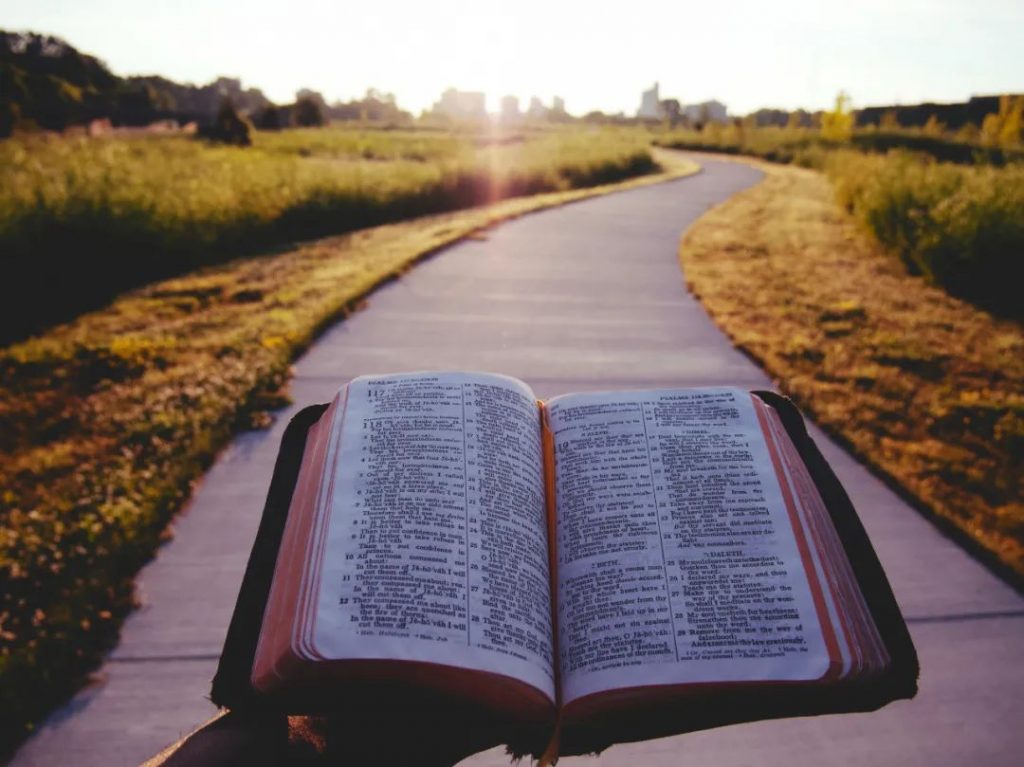
在这样等待的季节,我开始将诗篇翻过来调过去,一遍遍默读、默想。我无法祷告时,无力诉说时,诗篇便代替我的情感,赤裸在神面前。经文里的光景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哀痛、怀疑、苦闷、诅咒,被遗忘、被背叛、被憎恶、被追杀,所有等待救赎的过程,都被一一毫无保留记录其中。
赤条条的毁坏、坦白、无助、对处境的绝望、对神无作为的抱怨、对敌人的咬牙切齿,这些看上去如此不“属灵”的言语、心思、情感,却是神所爱之人的心声,是神所默示的。因祂不是要我们以自义的形象来到祂面前,我们内中有再多苦毒,将之一一倾泻,也好过冷漠转身背向神,更好过自我欺骗地对神说假大空的好话。如C.S.路易斯在《诗篇撷思》中所说:
“即使是最恶毒的咒诅,都能让我们从中看出诗人与神多么亲近。虽受表达方式的扭曲,一种属神的声音仍从这些咒诅诗篇中透露出来。”
因是对神说的,即使是在极致的情感撕裂中,抓住的绳子,依然是神。
是的,从某种程度来看,有正才有反,有彻底的死,才有真正的生。是否就是要在等待中陷入完全的无助,完全的死去,才能真正凭信心,而非“以为”呢?如果不将自己坏透的心完完全全敞露,看到其中一丝意义都没有,一点好光景都生不出来,又怎能真正认识和转向那知道所有、掌控一切的神?
人们等待戈多,是不断在现实的琐碎与焦躁中抓取线索,来猜想究竟戈多是谁、何时出现,但如此缥缈之希望,如何能在此刻降落。戈多不是死了,也不是没有来,而是人心必须先在此刻让位。不是未来,而是此刻。
若我总是期盼在将来某个时刻,一切都会完美,那此刻便是真正的煎熬,完全的无意义;然而此刻依然是真实的,顶天立地的真实。真实如我的感受,我无法掩盖,无法逃避,唯有直面,唯有记录。
如同那天,就在那逼仄的餐厅走廊里,在宇宙爆炸前的一瞬间,一个声音温柔生出:“转向我。”周围安静下来,我惊异,深吸一口气,在心里轻声问:“此刻,你想让我看到什么?”
然后我抬头,正对着我的是一方拥挤的收银台,一个中年模样、头发盘起、身穿红色工作服的女人,左耳和肩膀夹着电话,听着电话那头的点餐,双手迅速在计算机荧幕前左点右点,然后秒挂电话,又厉声喊道:“下一位!”
身旁的外卖长龙又向前移动,她头也不抬地听着对方报餐,出单、收钱、找零,转身电话又响起……来来回回,重重复复,看似机械、无聊,这却是她的一天。
如果眼前的外卖是我的等待,这是否也是她的等待?等待无数个订单的完成,等待收工,等待脱下制服,等待和家人同桌吃饭;然后此时此刻,她如此专注于眼前,如此纯熟、从容地面对这眼前逼迫而来的焦虑,而我专注地望着她,望见了她的生活,望见了神如何看她。
那瞬间,一种充实感从她那里传递过来。就在那一刻,当周围人目空于焦躁与手机之中,透过她,我看见了神。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3)在等待中,我逐渐更加明白,将自己倒空,让她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是被苦毒和焦虑所占据,而是让自己的以为慢慢死去;转而渴慕深一点,再深一点,在每日的生活中一点一点汲取恩典,在恐惧和焦虑侵入的瞬间,转身向神祷告。
有时候,一句话就够,不断重复,不是机械的无意识,而是想要让这句话由头脑进到心底,想要紧紧抓住,单单依靠,哪怕只是摸到耶稣的衣襟,就已经够了。
原来,当我真正静下来聆听时,内心深处回响的声音是,即使什么都不做,瘫倒的等待,荒漠中的无助,我依然是被爱的。
就在这里,在这一时刻,神的面就在眼前。


一、整体感受
这是我第二次参与创世纪文学奖的终审,我读到的是最终入围的13篇散文,整体来说,这些文章让我领略了好的文学作品给人的阅读愉悦。基督徒的世界观和生命观与常人不同,写作者观看世界与想象世界的方式也不一样,基督徒文学所呈现的情感、经验与想象,是独到的文学风景。
这些散文的语言,大都平易朴实,但作者对于人生、对于生命、对于人的思忖,非常深刻。有的作品的形式很有意味(比如《溪畔人生》,作者将一生当中曾经暂居的不同“溪畔”对应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溪流的风景与人生构成一种互释之关系),结构很有艺术性。
基督徒创作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只供给教会内的读者来阅读,它也应该在公共领域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与传播。面对这个世界,基督徒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督徒从圣灵而来的不一样的洞见,通过文学彰显出来。这是基督徒创作文学作品的动机。
然而,这些文字必须是文学,首先要有文学性。如果是小说的话,它首先不是说教,而是以感人的故事与让人唏嘘的人物命运来使读者沉浸其中。
如果是诗,更不能重复圣书教义或上帝的教导,而应是真正的现代汉语诗歌。即使在汉语诗坛,这个作品也能打动一些读者。
同样,如果是散文,也需要它有整体上的文学特征,不是说教,而是有美的效果、有动人的情愫或有奇妙的想象与思忖。
这13篇散文,首先看其文学性,我觉得它们首先是合格的文学作品。然后,这些散文里边的基督徒的灵性(对自我、人生、生命的态度与思考)、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遭遇及他们依靠神所呈现的应对方式,是非常动人的部分,让我非常受益。我想,即使是对基督教不甚了解的朋友,这些文字也值得一读。
二、关于《世界是双尖头鞋》
在所有的散文中,《世界是双尖头鞋》像童话故事中的水晶鞋一样,显得很耀眼。这篇文章从女性视角、从追逐时尚的这个世俗之风出发,对“世界”给予了不同的理解。作者说:
小时候看《灰姑娘》的故事,鄙夷恶姐姐们的削足适履,觉得她们非常蠢笨,而今天的我们,恰恰成了恶姐姐,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将我们自己变形,以适应“世界”这双尖头鞋。而“鞋”的意义,乃是让我们更好地走路,鞋是工具,但现在为了一种美,鞋本身成为目的。穿鞋不能走路,这就背叛了鞋的创造者,鞋已经不在其本位……这个世界如此,我们亦如此,我们都偏离了那被造的目的,我们都乞求一种叫“成功”的人生,总是削尖脑袋,让自己符合那些如同尖头鞋的法则。
这个文章的出发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穿鞋的事情,与每一个人有关,作者却有效地将尖头鞋与“世界”联系起来,一一道出其中的微妙关系。作者的叙述很有想象力,也很有文化视野,语言也很有当代性、很有趣味。作者对当代生活的时尚很熟悉,虽然没有直接道出圣书教义,但在这种趣味性的言说与很深刻的思忖之中,让读者有警醒:
“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与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在哪里失去了自由?
“我”是否已经迷失?
……
作为基督徒文学,通篇并没有与基督教相关的字眼,但作者思考的问题及传达出的价值观,却是深合圣书教导的。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堪称典范的基督徒文学。
三、关于《等待的“无意义”》
散文这一文学类型,有的以动人的情感取胜,有的以日常生活中的趣味取胜,有的以风景及对风景的感喟、思忖取胜。《等待的“无意义”》一文,首先是一种文化散文,作者很有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视野,熟谙加缪与贝克特这些现代文学大师的荒诞文学,也熟悉C.S.路易斯总是能切中肯綮地对当代世界做出思考,阅读这样的散文,读者有一种思想上的受益。
这篇以思想性取胜的散文,让人对“等待”这一日常生活状态有了重新认知。等待有时让人焦虑,无所适从,因为我们“总是期盼在将来某个时刻,一切都会完美”,若以这种心态等待,“那此刻便是真正的煎熬,完全的无意义”,“然而此刻依然是真实的……唯有直面”。
在这种“直面”的心态中,作者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能看到超越自我需要的情景、看到神的恩典。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之后,“等待”的状况也变得有意义了:“在等待中,我逐渐更加明白,将自己倒空,让她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是被苦毒和焦虑所占据,而是让自己的以为慢慢死去,转而渴慕深一点,再深一点,在每日的生活中一点一点汲取恩典……”
即使是非基督徒,阅读作者的思忖,也可能会积极地重新面对“等待”。
此文赋予“等待”以新的意义,作者让这一日常生活状况由焦虑、乏味变成了等待恩典降临的时刻。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造成无数人处于被“囚禁”的困境之中,“等待”变得更加普遍、冗长。作者的个人思忖,也因这一世界性的境遇,而成为了多数人的福音。

首奖:No 095 《老妪与宣教士》
优胜奖:No 103 《舅舅的故事》
佳作:No 033 《溺》
2022年创世纪文学奖终评意见:
我的评审打分和意见是参考组委会给予的评审标准,以此比重来考虑的。
1.信仰相关性(20%)
2.人物形象描述(20%
3.结构和情节(20%)
4.叙述语言与表达(20%)
5.思想立意(10%)
6.总体艺术表现力(10%)
首奖推荐:《老妪与宣教士》
在信仰相关性上,《老妪与宣教士》几乎可以得满分。这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以中国历史中真实的甲申教案为背景,通过描述洋人天主教宣教士与中国老妇人的故事,来呈现:宣教士当时的处境;基督信仰走近中国普通百姓时遭遇的文化障碍;以及地方官员在教难事件中的态度和角色。对于梳理历史,反思和剖析跨文化宣教中的张力都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在人物形象的描述方面,小说中的两个人物描述得都能立得住,内在情绪逻辑、思想逻辑,与外在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都相对合理。人物内在与外在的逻辑合理性是小说创作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也就是常说的,人物具有脱离作者意志和操控的自我发展趋向。即便是非常巨大的思想转变与惊人的戏剧化情节,小说家也要细致地处理逻辑合理性。小说中的阿婆尤其刻画生动,几乎呼之欲出。但人物的内在张力不够,人性挖掘不够深入。
这篇小说在结构和情节处理上中规中矩,是比较传统的叙事写法,缺乏现代小说的艺术性。其叙述语言与表达上同样如此,既可以说,相对其他作品来说更为成熟,故而我推荐为首奖;但同时,这种结构和叙述用在中篇长篇上相对更合适,用在短篇小说上,就略显平庸,缺乏现代短篇小说的寓言性、诗性、哲理性。这是作者在今后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可以加强的。
在思想立意和总体艺术表现力方面可以打七分。不知道董增德与阿婆的故事是否有历史史料的原型?如果完全是虚构,此小说的价值相对就弱了。因为,一来董增德是一个历史人物,而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用的是真实名字;二来阿婆不是一部中长篇中的一个小人物,而是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果事件和阿婆这个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并且没有历史原型,那么这里呈现出来的其实是当代人的想象,意义相对弱了许多。
如果有历史事件原型,建议加注。如果完全出于虚构,这篇小说又用了朴素的历史叙事手法,缺乏短篇小说的艺术性,也许首奖就要让位于《舅舅的故事》了。另外一个意见就是,这篇小说的名字需要重新考虑,目前缺乏艺术性和吸引力。
优胜奖推荐《舅舅的故事》
这篇小说的信仰相关性非常强,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其信仰性融于家常生活和人生命运中。作为基督教信仰小说,此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敢于用文学来触碰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有关抑郁、自杀等神学伦理学方面的议题。
并且使用文学的强调人性与情感、偶然性与未知性,来突破过于理性的、构架性、命题式的神学中的悖论。让信仰回到生命的真实状态,同时呈现出“隐密的属于耶和华”这样一种信仰文学的审美,这种文学审美恰好也与当代短篇小说的寓言性、哲思性的艺术倾向相合。
因此我认为这篇小说的尝试,是非常具有当代基督教文学实践和创新价值的,也是值得提倡的未来的方向。
小说的人物形象描述非常生动,并且娓娓道来,不着痕迹,并且字句之间没有低俗的煽情,却处处含有温情,并能够吸引读者产生共情,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小说在结构和情节上看似散,许多人物和场景是没有前后交代的片断,但这是因为小说的名字局限了读者的思维。这篇小说的真正主人公不是舅舅,而是“我”。
作者写的是“我”,小说中的舅舅、湘湘、梦梦等所有人,以及他们对于自杀的实施和各种反应,都投射在“我”的心里。如果从“我”这个角度看,小说就写得十分完整,是写“我”对于“自杀”的认知和感受,以及其成长变化。
不得不感叹,这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巧妙,可惜名字起得有点拙劣,对读者产生了误导。这也是作者创作不够成熟的地方,有可能小说最后的呈现,不是作者预先安排好的,属于“天成”。
这类情况其实在成熟作家中也常常发生,对作品的解读有时超越作家的认知,形成这种状况的基础就是真实、细微地呈现生活与情感的原貌。我在此小说中感到,作者写的是他熟悉的情感与生活,或者是他进入了他的小说世界。
作者的叙述语言和结构的细微处理上还不够成熟完美,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但这篇短篇小说更具现代小说的特性。
在思想立意和总体艺术表现力方面也可以更为提高,提高的方式就是“功夫在诗外”,如果要走出这条新路径,需要对所要表述的信仰伦理问题有更深入更多方位的思考。从起初的直觉性写作,渐渐成长为“冰山一角”式的写作,让文学作品建基于更为深厚的思想基础之上。
我个人认为《老妪与宣教士》和《舅舅的故事》总分是并列的,前者更为成熟,但传统;后者略显稚嫩,但创新,是未来的方向。犹豫再三,最后选择前者,是基于其故事具有真实历史事件原型,也就是加上了史料梳理的学术分数。
佳作奖推荐《溺》
这篇小说文笔很好,人物也生动,小说的艺术性也是基督教小说中比较高的。但我认为此小说有几个致命弱点,使我最终将它归入佳作奖。
小说的主体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信仰相关性,之后在台北听赞美诗、遇到中年大叔等事显得很突兀,因为没有写出合乎逻辑的内在情感和思想的发展线,小说也没有呈现出人物的张力驱动。
小说表面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确实掩饰了底层逻辑的断裂,容易让读者感到是篇不错的作品;但我个人认为,人物思想与情感发展的逻辑合理性是小说的“命根子”。
这种断裂如果不进行修补和重整,作为基督教文学容易出现表皮与内在脱离,出现“加个光明尾巴”“穿件信仰外衣”等现象。作为世俗文学,这类作品写得再好,也仍在习作范围内,难以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

以下不是要作结论,只因为我又误会了要作第二次交流,于是又写了一些,也就不浪费,交了上来。我没有改变我的名次。先改一下手民之误:
“阿婆为何恨主角神父?为何突然转为仗义行侠,挨揍也为神父搬请救兵?”应作“阿婆为何由恨主角神父,突然转为仗义行侠,挨揍也为神父搬请救兵?”
比较《老妪与宣教士》与《溺》:
初审时就考虑过让《出手》排名在《老妪与宣教士》之先,但后来《老妪与宣教士》得票最多,便置而不论;到决审时,《出手》出了局,《溺》入了围,我不得不将这两篇并列考虑。
《老妪与宣教士》与《溺》两篇,都以救赎为主题。首先我同意张老师所说:“全篇(《老妪与宣教士》)的叙述语言略粗糙,为讲述而讲述,成语和概念化的用词过多”。
为什么呢?我以为它加上了历史背景,故情有可原。语言的抉择,古今调度,较所有入选作品都要复杂,作者的功夫也见出于对白设计,生猛幽默,又有生活气息,表达人物的性格,极具感染力,或许,补了叙事语言的“缺憾”。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缺憾”,因为作者是否刻意保留十九世纪的语言特色?于是,本篇有了两套语言,是有点不搭档。但那就是另一个题目的讨论了,目前起码没有全部语言都毙掉。何况作者前期资料搜集,还是用了苦功,毕竟要技多一筹。
关于主题与人物的关系,《溺》的福音置入位置充满了偶然性。虽然我也考虑过莫非老师评说的男主与中年大叔角色的对比性,一是受益者未必领情,另一是救赎者的心甘情愿,来达到点拨少年阿杰的艺术效果。
但是,始终,这不是由主角推展出来的剧情,就不如《老妪与宣教士》的人物生动,彼此互动,一起推展剧情,类近神人互动的模式,那也是类近旧约与希腊悲剧的叙事模式,不可视之为陈旧。
正因为如此,小说主人才可以改变或成长。《老妪与宣教士》的两个角色都有改变,此便是成功之处。《溺》的主角虽然也有所改变,但后来也不见大叔的角色,仿佛他是个过场人物。作者安排男主的人生路上,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时空出场点拨他,设计便有点像《天路历程》,于是,小说的模式又变得旧起来。小说的成功关键在于人物,因此,《老妪与宣教士》这方面又稍胜一筹。
至于结局,两者的人物发展都有草草收场之憾,老妪的突兀改变还可决诸长时间的因素,以及隐晦的叙事观点,以作掩饰。《溺》如张老师所言“阿杰的转变略显仓促”,因为没有以上两项的优势,便与它之前的叙事节奏脱了节。因此,《老妪与宣教士》又微胜。
说到故事,《溺》又给《老妪与宣教士》比下去,前者求淡,后者求浓,这当然与取材的时空背景有关,又是风格的差异。例如,后者两个人物都在不断推展救人行动——身体与灵魂救赎,互相交拼,火花四溅,动态情节,自不同于“溺青”心理意识活动的静态呈现。
当然,我们不能说James Joyce(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就一定输给情节跌宕的金庸小说(我就十分喜欢前者),但是评审就是有“结构和情节”的要求,还占了20%;身为评审,只是法官断案,也就只能服膺于法律了。
因此,这部分,我也不得已把很James Joyce,很契诃夫式的《舅舅的故事》拉下,就是因为赛制所限。我本来将《白鹭》《玛丽的旷野》列为首二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主角推动情节,没有偶然情节,干净!结构较目前这三篇都要严谨。
另外,关于题目的艺术性,无可否认,《溺》的象征意味,反映了作者加了工,花了心思的设计,象征了阿杰被救之后的感觉,生命一溺没毙就一直溺下去。不过,老妪代表了守旧的上一代,无法接受新的外来文化;早期宣教史上,宣教士常被认为是文化的改造者,甚至被误会成侵略者。于是,老妪与宣教士是两个统称名词,统摄以上复杂的寓意,甚至超越地域限制,成了文化符号,因而制造了对比的张力,未必没有艺术的考量。
所以,两个题目,我觉得起码可以打个平手。另外,现代汉语少单音节词,如裤子、桌子,而不是裤、桌,理由很简单,如果光读不看字,一开始就自制歧义:是腻?匿?逆?暱?昵?还好不是“东”字。《溺》从音节考量,又稍逊一筹。虽然这不是绝对性的,但写作人要小心无意识制造这些不必要的歧义。
因此,我还是让《老妪与宣教士》胜出。
→→→
经过讨论、交流,最后123名投票结果:
首奖:No 095 《老妪与宣教士》
优胜奖:No 033 《溺》
佳作:No 103 《舅舅的故事》

施玮
▽
诗人、作家、画家、学者。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在美国获硕士、博士学位。出版著作《叛教者》《红墻白玉兰》等十八部,获多种文学奖。于三十年间,历任各种报刊、图书之编辑和主编,在北京等地多次举办个人诗画展。
莫非
▽
作家,创世纪文字培训书苑主任,散文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散文奖”“梁实秋文学奖”等。小说曾获大陆“冰心文学奖”、台湾“宗教文学奖”等。著有文字事奉系列《天国的影响,上帝的时间》等四书;散文、短篇小说等十余本。
张鹤
▽
笔名书拉密,文学博士,曾任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硕士生导师,现为独立作家、评论家、编剧、翻译,出版、发表各类体裁作品数百万字。2017年创办“世代箴光文学创作工作室”,训练和陪伴热爱短篇小说创作的写作者。
齐宏伟
▽
比较文学文学博士,道学硕士,牧者。2000年领受“让汉语充满灵性”的感召,从而笔耕不辍,在海内外正式出版四十余册书。近期出版《叫醒装睡的你》和《寻找感动力》等,深望依靠福音真理和圣灵大能唤醒昏睡浊世。
罗菁
▽
香港岭南大学哲学博士,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圣经研究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剧场历史与批评硕士,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学士。长期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教授剧场表演、剧本赏析与剧本创作、创意写作等课程。

